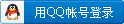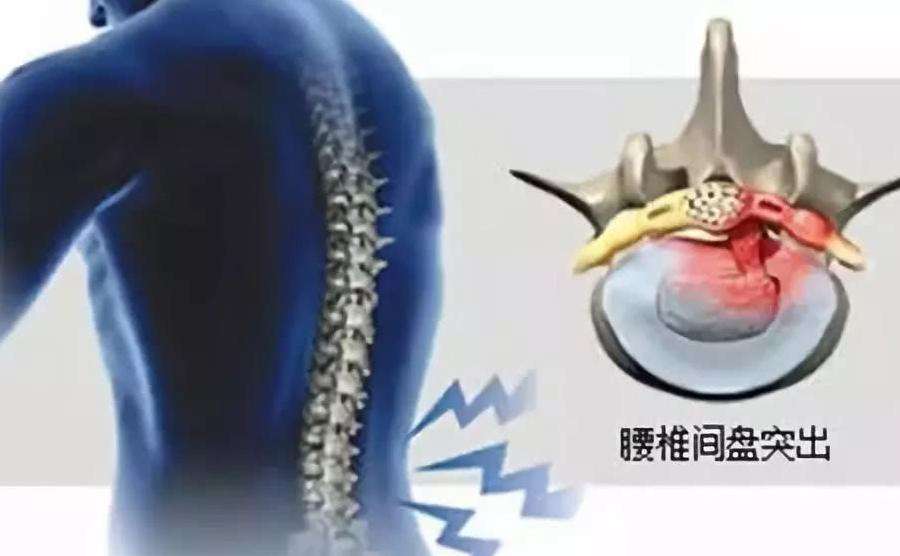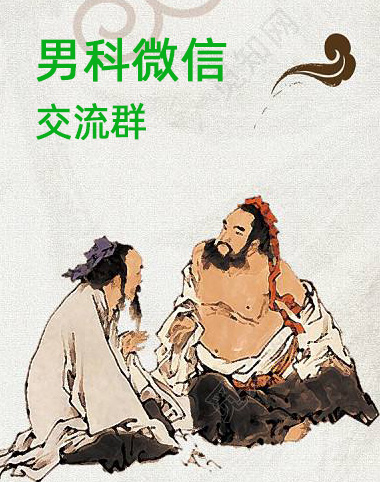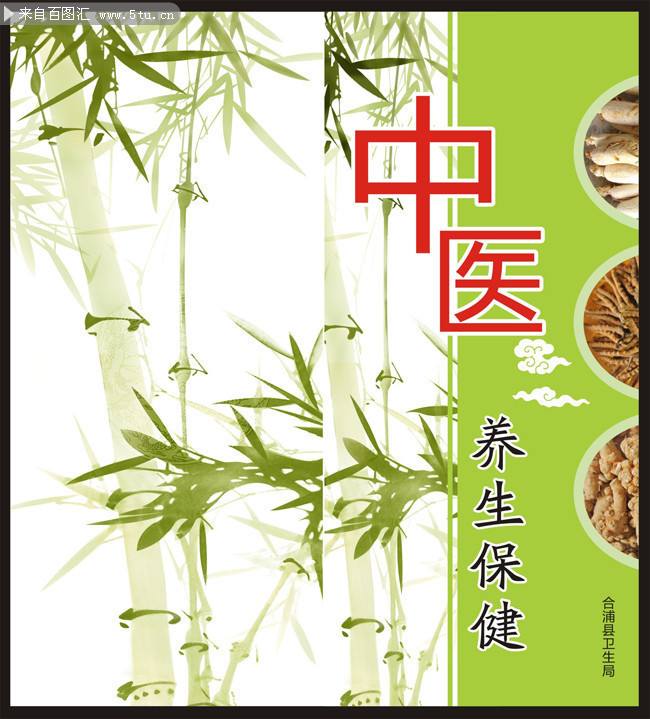这里是《人物》的「见好」栏目,编辑部成员会有主题地分享一些亲自体验过的好物好所在——日常,我们一起分享故事,今后,我们也要与你分享生活。本期《见好》主题——你心中的那片海。
「3.7亿年前,一群勇敢的鱼终于决定离开熟悉的海洋,爬上陆地,开始新的生活,它们从此改名为『四足动物』,而其中一个遥远分支就成为了正在阅读这段话的人类。」这是我们采写古生物学家张弥曼稿件中的一段话。我们和大海之间那种若有似无的亲切感,是刻在基因里的。
生活不易,在这个并不是特别方便出行的夏天,大海依旧是不该缺席的存在,总之,一起看海吧。
策划 | Yang
编辑 | 金石
地点:宁德三都澳
分享人:秋秋
作为一个渔民的女儿,我的记忆就是从咸湿的海风开启的。我们的家建在海上。那是一种神奇的建筑,粗木排绑上大泡沫球,得以浮在海面上,连接成网状的「大陆」。薄木板搭成的小房子连年漂在海上,是我和爸妈的家。
关于那片海的记忆可太多了。夏天的时候,可以躺在木排上乘凉,抬头就看见漫天的星星。身底下是广阔的海域,耳朵贴着听,可以听见海鱼扑通扑通的声音。远处偶尔开过一艘大船,海浪涌过来,整片大陆就上下摇摆。记忆最深的是房子里的茅厕,其实就是在木排上开个矩形的洞,如厕时往洞里看下去,墨绿的海水里有鱼在游来游去。爸爸告诉我他抓到过水母,真的会发光放电,我期待了好久,却从来没有等到过它们。抓螃蟹、甩饵料、捉海星、帮爸妈捞鱼筐里浮白的死鱼,都是关于夏天和大海的美好记忆。
渔排上的渔民很少吃到菜,如果远远看见送货的船,我妈就会兴奋地牵我去船上买方便面,爸爸随手从鱼筐里捞起一只金灿灿的大黄鱼,切段,煮进方便面里,人间美食。等冬天了,爸妈不让我再去渔排,我会被送到岸上的奶奶家,每天都眼巴巴等爸妈回来,凑近一闻,满身腥味。
渔村的名字叫「虾荡尾」,因为我们坐落在渔岛的最尾部,像一只小虾摇荡着它的尾巴。去厦门看到白城沙滩以前,我对于海水的记忆一直是绿到发黑的颜色,怀疑是不是因为大人们偷偷往海里排汽油,所以让海看起来那么黑。我记得,天气一热,所有的小孩聚在码头,一猛子扎进水里,脸晒得通红,黏着盐粒。后来,海水受到了污染,鱼的收成越来越差。做渔民苦,大多数渔民回到岸上、城里,做起了其他体力活。我上三年级后,家里把渔排卖了,那片海上再也没有我的家。
前几年,我回虾荡尾见奶奶。在去的船上,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标志。船驶近一看,那是某家电信服务商的营业厅,它孤零零地漂在海上。我噗嗤一声笑出来。
地点:普吉岛查龙码头
分享人:罗二狗
我喜欢海。大概每一个内陆城市长大的小孩心里都会有一个大海梦,翻着《十万个为什么》,边午睡边幻想,海到底有多大呢?跟天空真的是连在一起的吗?真的会有避水珠吗?潜入海底的话会不会有龙宫?
等稍微长大了点,有了跟大人出去玩耍的资格,大海的神秘感一点一点消失,它更像是一个游乐场一样的存在。去海边,意味着夏天,阳光沙滩,晒脱皮的手背,椰汁冰棍,最惬意的是傍晚坐在露天小饭馆,大人喝冰啤酒,小朋友们沉迷于辨认各种螺。
工作了之后,海边好像成了避难所。三五好友约着出去旅行,总喜欢奔着海去,那是结结实实的老年游,半中午醒来,佛系浮潜,看看夕阳,一边吹风一边聊一些没有边际的天,饿了就溜达去吃宵夜,几天嗖的一下过完,然后在回程的飞机上默默期待下一次海边之旅。
因为职业的关系,这几年也渐渐见到了海的残酷一面。
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在青岛的海边,一位老人因为被保健品公司骗走了所有积蓄,想不开跳海了,遗体找到的时候,能辨认身份的东西是裤兜里一张写了名字的红纸,那是某次参加保健品会议留下的姓名牌。
2018年夏天,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47位中国游客遇难,我连夜飞去普吉,在那里遇到许多同行,我们一起登上了搜救的军舰,在海上看救援人员作业,回到岸边,又一起坐三轮车赶往医院。我们见到那些所谓的幸存者,他们多数失去了至亲和挚友,没有遗言,没有遗物,甚至连这次游玩的照片他们都没能留住,和手机一起永远地留在了海底。
印象很深的是,在普吉岛那些天,查龙码头晚霞总是特别热烈,海风吹来,栈道上有人遛狗,有人跑步,生命无常,而生活总是一直往前。
地点:日本冲绳、淡路岛、北海道稚内
分享人:小叉
沿着海岸线一路从南至北,在日本能看到三种颜色的海。每次惊叹海还有这么多颜色的时候,总是会遇上有趣的人。
最南边冲绳的海是绿色的,尤其在古宇利岛附近看海,色彩的冲击更强烈。冲绳本来就是奇特的存在,不同于日本本岛,这里充满琉球王国的野性痕迹。人们喝着日本最烈的泡盛酒,赏着全日本最早开的樱花,连信奉的神兽都是张牙舞爪的狮子。
在冲绳第一次看海,沙滩上,一个路人老爷爷自告奋勇地要帮忙拍照,完全没有了日本人的社恐。他是冲绳土著,70多岁,刚从便利店买了挤满番茄酱的热狗,吃完要找老同事喝酒去。白色棒球帽,正方形的眼镜框,宽松的棒球服,很嘻哈。临走的时候,他嘟囔几句,「你们看,冲绳的海是绿色的吧。东京大阪什么都市可是看不到的。绿色的海才能治愈人,绝不是蓝色那么普通。」他还给我们推荐了海边小饭店的猪脚荞麦面,「要配上老板娘做的烧酒泡辣椒才过瘾。」吃完面,兴冲冲打开手机一看,呀,老爷爷一张照片没给我们拍上,全是他的自拍照,嘴都咧到耳根了。
濑户内海是典型日剧里的海,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湛蓝。淡路岛是濑户内海上最大的岛屿,那年去淡路岛正值秋天,听说住处附近的海上日出很好,于是,我起了个大早。起初,海是灰的,突然太阳从海平面上跳起来,一切都变蓝了。旁边几个日本女生看到这一幕大喊大叫,我不禁朝她们多看了几眼,结果被拜托拍照。一个女孩说,暗恋的男生是淡路岛人,他的家人在阪神大地震中去世,因为想要了解他的过去,特意从东京到这边旅行。分别时候,她强烈推荐了淡路岛一家海边露天温泉,可以一边看海,一边泡温泉,「他告诉我,秋天红叶满山的时候,最适合泡温泉了。我打算去试试,你也要去哦,濑户内海全貌一定非常温柔。」再去那家露天温泉的时候,并没有遇上她。但后来每次想到濑户内海的温柔蓝色,我怕都会记起那个女孩子。
一路向北,到了北海道稚内的鄂霍次克海。这里的海一点都不温柔,藏青,蓝得发黑。
在猿拂村海岸上,600平方公里的村落里只有2000多个居民,下午四点多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迹。附近有一片牧场,几十只奶牛们挤在一起。海边立了一座奶牛感谢碑,大意要感谢村里奶牛们的付出:它们可是全村家庭最宝贵的存在。
几个招待独自旅行者的小木屋门口停了很多山地车,有个大叔偏不住,把越野摩托一停,自己在牧场上搭起帐篷。因为着迷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族的文化,他从道南骑行而来,「到了这把年纪不服老不行,但看看这里的海,又觉得人生充满了干劲呢。」明天,他要骑到终点——日本最北端的宗谷岬,那里可以越过鄂霍次克海看到俄罗斯的库页岛。问他抵达终点后,第一件事打算做什么。大叔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可是站在最北边的土地上。这种事情,当然第一时间要打电话和我家夫人报告。」
从南到北,人们都说一样的语言,却和海一样,各人有着不同颜色的故事。回忆这些海的样子,其实最美妙的还是在海边遇到的人呢。
地点:夜晚的青岛
分享人:三浦野边
作为湘中土人,对海我没有概念,基因里只有山和湖。但海是最好的疗愈品,人类一点就通。
去年5月,偶然读到老舍散文,关于青岛(正好在手边,请允许摘抄一段凑凑字数):五月的海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的走,燕低低的飞,街上的花香和海上的咸混到一处,浪漾在空,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
春深似海,多好的词。因为这个词,当即买了一张去青岛的票。但买完后,又因为生活里琐碎的麻烦事给忘了。重买一张票之后,当晚住进了青岛一家民宿。老板说,惊不惊喜,今天只有你一个客人。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有人相爱,有人夜里开车看海。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呢?」为了得到答案,我打算夜里一个人去看海。
晚上十点,青岛街上已经没有车,下了出租立即只剩我一个人。我打开和朋友的语音连线,给自己壮胆。往前走时,觉得像失明一样恐惧。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巨大的、压迫的黑。往前走是走了多远呢?大概一米。现实是,立即夹屁股打车回去,总共待两秒。
我看到了知乎那道题下面最好的答案。
「别在那瞎文艺,夜里看海的都是傻子,黑漆漆一片就是水声,在厕所里关灯冲马桶是一个效果。」
地点:长滩岛
分享人:葡挞
那是在长滩岛。风逐渐扬起,我穿着救生衣,坐在船上,手扒着船沿。看着同行的朋友一个个戴目镜、咬着呼吸管,下船梯,慢慢荡开,把身体交给大海,玩得很开心,我也终于决定下水。
因为不会游泳,我拉紧了救生衣的带子,一下水就牢牢抓住了绳子,在船周围两米的水域里,我好像获得了自由,想要往更远、更深的地方去。我松开了绳子,离开船,尝试平躺在水面,让浪推动身体,偶尔脑袋在水下,但因为呼吸管伸出了水面,所以一切都很惬意。
直到一个浪打过来,海水从呼吸管进了嘴,那是我第一次喝海水,终于知道「苦涩」这个形容词的实际含义了,喝一口就被呛到,于是又呛了更大口的海水。在同伴拉我回船的路上,我再一次被浪打中,吞了海水,被折腾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是不是要死了?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死了吧?这是我死前的想法吗?真是毫无想法啊……
但可能是那次的海太好看了,我没有因此想远离水,而是下决心要学会游泳,尽管过了两年,我还是没学会,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露出苦涩的微笑。
地点:辽宁锦州
分享人:八月妹
听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被套上个大游泳圈,在东北的海里扑腾了。长大后,我看到儿时的照片,那黑色的海(浪),粗硬的沙子,瘦猴般的我,实在无法与我们对大海的美好想象挂钩。
终于有能力四处旅行时,我非常沉迷看海,从地中海到印尼的热带,加州的海到加勒比的海,都蓝得各有风情,我也在各处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而回到故乡时,家人每每提议去海边玩,我就兴致寥寥,脏海有啥可看的?
终于有一次,我跟着父母去赶海,在很多年后重新审视北方的海。父亲开车驶过码头,他们说,渔民兜售的螃蟹越来越小了,如今的北方饭桌上盛行一种说不出种类的鱼,叫「扔吧」,通常做酱卤味道。过去渔民打捞上「扔吧」,看都不看,直接放生,现在却成为一道受欢迎的家常菜。我们来到海滩上,母亲拿出自备的铲子开始挖蛤蜊,父亲到礁石旁下螃蟹笼,满海滩的人都在奋力从贫瘠的海滩中寻找生物的踪迹。
一个上午过去了,我们收获了半桶小蛤蜊和两个可怜的小螃蟹。每当这时,他们经常说起,以前不是这样的,周六日到海边,随便挖挖,就是满满一桶海货,若是到渔民处购买,一桶五块,不用还价,拿上就走。
我逐渐意识到,随着我的长大,故乡的海在人们的索取下正在变得枯竭,它令我感到难过,丰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有些东西被我遗忘了。去年,我写了一篇发生在东北的报道,重新认识了我的故乡,如今,写下这些,翻出老照片,看着在我还是个婴儿时就张开怀抱迎接了我的大海,我从未觉得它如此珍贵。
地点:柬埔寨西哈努克
分享人:猫腿
作为一个内陆地区长大的人,我从小就对海有着莫名的憧憬。
这两年去了位于垦丁国家公园最深处的海。隆冬季节的太平洋,可以用凶悍两个字来形容。天气阴沉沉的,礁石林立,海风锐利,向刀子一样割脸。站在悬崖上往下看,望而生畏。
在游客的刻板印象里,海面总是宁静的,有椰林,游人和齐全的各类娱乐措施。不过,凶悍,可能才是地球上绝大多数海面的常态吧。
还看了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的海。抱着和朋友在海滩上一坐一整天的期待,我们欢快地预定了带有沙滩的酒店。果然非常符合我们对于海的设想。刚躺下没多久,就有皮肤黝黑的柬埔寨阿姨拎着箱子,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做除毛。她们看起来一脸狡黠,报了一个听起来并不高的数字,并迅速拿出了全部工具。一行三人像傻了一样乖乖就范,躺在沙滩上,动都不敢动,任凭她们处置。用的是传统的棉线,很疼。
最后算账,发现其中一位姑娘的价格比其他人要多一倍。当我们询问原因时,阿姨用十分不熟练的散装中文,手舞足蹈说,因为,你毛很多,所以,两倍钱。
真是不愉快的一次海滩消费。想来这种被开发到位的海滩,多多少少都有此类诱人消费的陷阱。以前看超级女声,曾轶可用「野海」这个自创的词来形容游客罕至、未经开发的海。这么一看,真正可爱的,还是那些野海啊。
地点:印度尼西亚东北部
分享人:尹夕远
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片海的具体位置,它在印度尼西亚东北部,靠近巴布亚省。我们每天沿着赤道航行,有时在北半球,有时在南半球,那是我见过最平静的海,由于处在赤道无风带,那里没什么浪,太阳和月亮同样温柔,阳光是金色,月光是橙色,而海面像一块铺平的深蓝色地毯,波纹同等大小,一排排向前匀速推进,有一种孔雀羽毛般的秩序感。
无比平静的海面 左滑看更多
连续一周的时间,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其他船只,与世界失联。每天从一句「今天海面平静」开始,到一句「今天晚霞真美」结束。这之间是三次下海潜水:望不到边的珊瑚峭壁,即使世界上最贵的相机也还原不了它们的色彩;蝠鲼张开宽达两米的双翼,在沙地中央清洁身体,翻转的时候轻轻抖动翅膀,像鹰,那瞬间会以为天空和海洋颠倒了过来;还没长大的小鲨鱼们会在浅水的海湾玩耍,有了危险就躲进红树林附近盘根错节的海底森林,但是几块冷冻的石斑鱼就可以把它们再次勾引出来。在距离水面10-30米的区间里,这片海疯狂的展示着其生物多样性。海平线之上,船像孤岛,可是一线之隔,却早被纷繁的生命包围了。
夜里我们不潜水,就躺在甲板上看星星和月亮。当月光最亮的时候,老船工开始唱歌,手中弹起木吉他,靠在船头,歌声和月光一起顺着黝黑的皮肤流淌到甲板上。
偶尔结束与世界失联的状态,不是因为手机有了信号,而是船航行到了有人的岛屿,一百多人的小村庄,村长站在沙滩上看孩子们玩耍。距离岸边几十米的地方,有几段破损的木桩孤零零插在海里,村长说那是他们村子以前的位置。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让我感到惊讶,在此之前,全球变暖议题只存在新闻和讨论之中,而那一刻我就踩在它的证明上。
我给岛上的孩子们拍照,看到相机,他们兴奋起来,翻着跟头展示自己的跳水技能。他们生活在这里,可能并不清楚自己的家园一步步缩小的根本原因,网络世界和工业文明与他们隔着一片海的距离,这片海吞噬他们,也保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