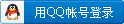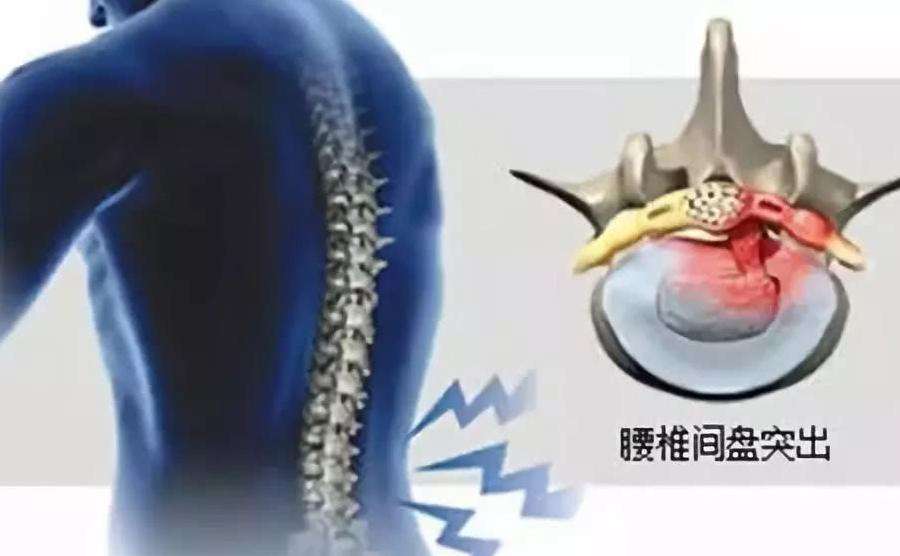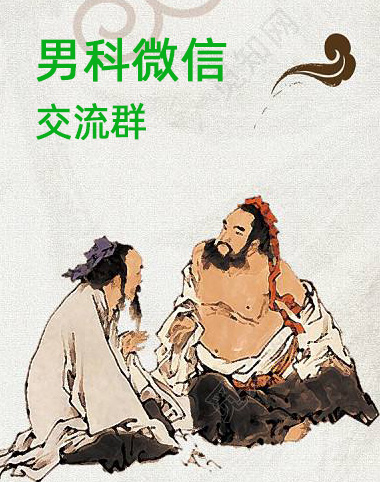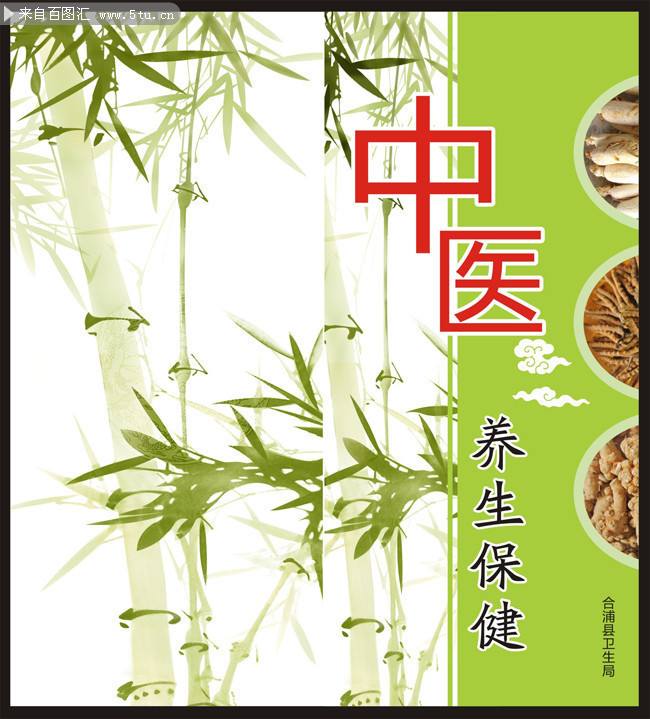【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上周,退休警察老董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往事。
卢沟桥大家都知道,北京城西南,永定河上。卢沟桥往南没多远,是107国道和京港澳高速,两条出入京要道。
这里有个杜家坎收费站,以堵车闻名,有人称其为「杜大爷」。
1996年,杜家坎一带有很多常年积水的沙坑,可以钓鱼。有一天,老董接到刑侦队命令,说杜家坎沙坑里发现一条腿,让他去捞。
那年老董刚干警察,在北京市局潜水队,专下水捞东西,证物、凶器、残肢、尸体,包括但不限于。
沙坑不小,水草连成片,一眼望不到头。
老董和同事划小船到水中央,扒开草窝子,看见了那腿,正安安静静卧在那儿。那灰黑的腐坏的肉的颜色——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老董说。
连草带腿扥上船,只一碰,腿就散了,只拎起了两根腿骨。不知道泡了多久,法医都检不出什么了。
这是老董第一次接触人体残肢。
后来一次,下河捞溺尸,第一次捞到了完整尸体。
河里水浑,能见度极低,人在深水里只能看见黑,彻底的黑。老董只能用手摸,以手感判断碰上的是什么。
待在潜水队的四年,最害怕的就是在水里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如果能远远看见尸体,就心里有底儿,游过去拿绳捆了就行。尸体算不得什么,唯物主义者不怕这个。
老董一摸就摸了四十分钟,什么也没摸着,紧绷的神经早松弛了,心里也琢磨其他事儿去了。
就在这时,一件东西磕在脑门上,老董一哆嗦。定睛一看,自己正撞在女尸面盆一样的脸上,手里正抓着一缕女尸轻舞飞扬的头发。
老董噌地一下,蹿上水面。
讲老董的故事,算个引子,就像从前说书人开场时的「入话」,暖个场。今晚的《北洋夜行记》,则是从苏州河上的半具浮尸讲起。
不过,那半具尸体一点也不吓人,甚至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回故事里的一个古怪男人。他搞得我太爷爷都产生了自我怀疑。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民国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清晨的苏州河上飘着一层薄雾,老垃圾桥边,一个老船夫正在整理缆绳。
近来,苏州河上的船只越来越多,水面越来越脏。除了像船夫这种渡船,还有货船、垃圾船、穷人的船屋,各种各样的船只停靠在岸边,本来就不算宽敞的河道,变得越来越拥挤。老船夫整理完缆绳,拿出一个旱烟锅子,猛吸了两口,坐在船帮上歇息。初春的天气,还没有回暖,河面上一片灰蒙蒙的,显得冷清,只有黄铜烟袋锅子里蹦出的火星,让人感觉到一点暖意。薄雾渐渐散去,远处的桥洞底下飘过来一个东西,像一截木头。老船夫并没在意,直到其他船夫纷纷从船帮上站起来,探着脖子看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老头也站起身子望过去,那不是截木头,是个死人,穿着一身条纹西装,后背冲着天,倒扣在水里。这死人慢慢漂到老船夫的船舷边,轻轻磕了一下船帮,停了下来。老船夫身吸了口烟,定了定神,心想着不知道又是哪个薄命的人,他收起铜烟杆,抻出一根钩芉子去钩。老头先用铁钩子杵了杵,没反应,铁钩子穿过腋下,老头轻轻使劲儿,勾胳肢窝,慢慢往上拽。老船夫瞧见这死人只有上半身,手上一滑,差点掉下去。得亏旁边船上来了几个小伙子,过来帮老船夫。等快捞上来,老船夫一看,咳了一声,竟是个放在百货商店里的人体模特。水中漂浮人体模特示意图。图片出自蔡明亮导演的电影《河流》。
老船夫把这个模特拽出水面,往甲板上放,模特下摆哗的裂开,一阵恶臭,一堆下水倒在了船板上。这个木头做的模特身体里,包裹着一堆内脏,不知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已经长满了蛆虫。
老船夫拿铁钩子拨拉几下,看起来是人的心肝。天气忽冷忽热,每晚睡得都不踏实,一直在做梦,梦到自己僵直无法动弹,醒来总会有一侧的身体发麻,肌肉酸痛。苏州河上发现无名尸块的事儿,很快在望平街传开,小报上传的铺天盖地,有说是招魂仪式,有说是连环谋杀。像样点的大报社,登出来的消息就靠谱一些,据传警察根据模特身上的衣服,查到了霞飞路上的一家西服店,西服店的老板已经传唤至巡捕房。看到报纸消息后的当天下午,一个穿着考究的女人走进我的事务所。这个女人进屋开门见山,自称李雪宁,是淮海路麟昌西服店的老板娘,他丈夫陈德明,上午被巡捕带走,接受审讯。李雪宁来是想让我帮忙替他丈夫洗脱罪名,按她话说,她的丈夫绝不可能杀人,也没理由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情。说完,她往桌上放了一个信封,她说这是一半的调查费,查出真相救出她丈夫来,付另一半的钱。这女人是真阔气,话说回来,在上海滩置办一身洋行头,也要百十来块钱,洋装裁缝做一套衣服就能挣几十块钱。我接下这个案子,跟李雪宁了解了一些情况,打算第二天先去陈德明的店里看看。陈德明的麟昌西服店在淮海路上,在上海,最高档的西服店大多集中在南京路上,淮海路和四川路上也有很多,档次就稍微次一些。这家西服店的档次在上海算是中等偏上,我去的时候,店里有两个学徒正准备闭门歇业。老板让巡捕逮走了,两个学徒还没出师,生意暂时是没法做了。我进店里跟他们道了个辛苦,又给他们一人递了支烟,跟他们打听一下陈老板的行踪。两个小兄弟接过烟,也不见外,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这个陈老板,不是上海本地人,年轻的时候只身来上海打拼,起早贪黑的,人到中年才好歹干出了这么一间临街的门脸。“陈老板家是世代做裁缝,我们师爷以前还是做官服的呢,听说那时候比现在挣得还多。”一个学徒说起来有点羡慕。我又问了问假人模特的事儿,他俩不像刚才那么痛快,不愿多说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受老板娘委托, “我查清楚了,你们老板早出来,你们这生意还能早开张不是?”徒弟们琢磨半天,其中一个跟我说,“别的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老板在出这事儿之前,好几天都不在店里,感觉他出完车祸之后,就对店里的生意不怎么上心了。”原来陈德明在半年前出了车祸,导致左腿截肢,休息了很长时间,这个月才恢复生意。小徒弟还说,陈老板在维尔蒙路还有个自己的裁缝铺子,平时做活都在那里,那里也有不少假人。
我离开西服店,沿着霞飞路往裁缝铺子走,眼睛余光扫到一个人,穿着一身棕色的西服,松松垮垮,不怎么合身。刚才站在西服店门口的时候,我就见过他一回,他站在街对面的一个书摊边,那会儿我还没注意。看到前面有个饭铺,我拐了进去,要了一笼下沙烧麦,坐在门口桌子边。下沙烧麦起源于明代,是上海浦东南汇地区代表小吃,有咸味、甜味两种。咸味以新鲜春笋、鲜肉和猪皮冻为馅料,甜味烧卖用豆沙、核桃肉、瓜子肉和陈皮制馅。
他老婆李雪宁来我事务所的时候,给我带来一张他的相片,我认得他长相。陈德明本人比照片上还要瘦一些,脸色泛白,戴着一副银边圆框眼镜,看着就是常在案头工作,很少到室外活动。他身材不高,穿着一件白衬衫,带着套袖,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马甲,左腿裤管空荡荡地垂下来,要不是我知道他截肢,真一眼看不出来他身体有疾。他不拄拐,仅凭着右脚站立,给我开门的时候,我俩都挺惊讶,我没想到屋里有人,他可能也没想到有人来找他。把我让进来之后,他一步一步蹦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我向他解释了一下来的缘由,告诉是他妻子委托我来帮忙调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从巡捕房出来了。陈德明伏在工作台前,头也不抬,听我一个人说,也不搭茬。只是皱着眉头,看着桌上的布料。“麻烦你一下,能不能帮我量一下我的肩宽。”这是我进屋以来,陈德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把桌上的皮尺递给我,“我量了好几次,都量不准。”我莫名其妙地接过皮尺帮他量,“谢谢,我在给自己做一件西服,你说你是来……”我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件事我已经跟巡捕房的说清楚了,我告诉他们这的确是我店里的模特和衣服,但是因为这个模特的关节脱扣了,这个假人早就扔了。我也不知道假人里怎么会有人的内脏。”他又埋下头,计算着数字,在布料上划着一道道辅助线。我又问了几句,陈德明都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要么干脆就是没听见。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块布料上。我环视了一下他的工作间,这间屋子不小,靠墙的架子上码放着布料。一个靠窗的角落堆放着许多卸开的假人模型,做的很逼真,乍一看还真有点瘆人人。我走到窗边,摆弄了一下这些假人,有些胳膊腿上还连着线,上面干干净净,没有灰尘,看来经常用。我又问了陈德明一些问题,他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有没有人跟踪他什么的。陈德明总是忽略我的问话,基本上都是问了一遍又一遍,他才反应过来,说他没注意过。我心想也是,就算一个大活人站你身边,你也注意不到。陈德明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块布料上,我觉得实在问不出,和他道了别,临走嘱咐他想到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顺手往他的工作台上扔了一张名片。陈德明一下子生气了,“你这人怎么乱扔东西,你是谁?为什么来这儿?”我一愣,合着刚才说的话他都没在意,我先道了个歉,又把他老婆委托我的事儿说了一遍。我下了楼,刚出公寓门,那个棕西服又出现了,他正在街对面的水果摊边,仰着脖子盯着二楼陈德明的工作间。他看到我出来,急忙低下了头,把手中的拿着的苹果扔回水果摊,急匆匆地走了。我赶忙跟上,就看到棕西服刚拐到霞飞路上,冲着南市那边去了。我紧跑两步,追上去,想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在快到租界和华界分界的民国路路口,他回头扫了一眼,好像看到了我,加快了脚步,冲进了旧城老街嘈杂的人群中。我紧跟慢跟,转得头晕,还是跟丢了,老城里人太多,挑挑担担儿,人来人往。我站在路边喘气。城隍庙边的九曲桥上,戏台上正唱着一出滑稽戏。城隍庙戏台上的滑稽戏,开始演的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演着演着,不知怎的,戏台上的演员开始说起了北京话,我打眼一扫,旁边的街景也变了,这不是上海的城隍庙,是北京隆福寺庙会搭的戏台。

隆福寺庙会是旧时北京著名的定期市集,每月开庙十二天或十三天。每逢庙期,上至在附近王府居住的贵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下至贫苦市民和近郊农民都来赶庙会,购买土特产品,吃小吃,观看戏曲节目。
戏台上的人唱的也不是《啼笑因缘》了,而是我之前查的案子。戏台上的金木让人五花大绑绑了起来,另一个角色指一指台上的金木,又指了指台下看戏的我,哈哈地乐。我想冲上台,使劲挪动两条腿,却怎么也动弹不了,我低头一看,从两条腿上抻出了两条线,再一看我的胳膊,也有两条线。这几条线抻过我的头顶,我一抬头,天空中浮现着一张巨大的脸,是陈德明的脸。一脸讥笑地看着我,他的手里攥着控制我四肢的线。我想摆脱,四肢却怎么也使不上劲,我就像陈德明的提线木偶一样,在戏台下做着滑稽的动作,而戏台上,那个演员举起了一把枪,对准了台上“金木”的脑袋。“嘭”的一声,我从事务所的沙发上摔到了地上,摔得我半边身子发木。从城隍庙回来,总感觉心神不定。我没回家,直接回到事务所,把当天查的东西记录了一下,想理出一些头绪。在沙发上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还坐在沙发上回味着刚才做的梦,电话铃响了,惊出我一身冷汗。没等它响第二声,我赶忙接起听筒,对面的人喘着粗气。然后就是粗重的呼吸,我连问了几声,对方都没有应答。我披上一件风衣冲下楼,凌晨两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想拦一辆黄包车都拦不到。我跑了十分钟,终于跑到维尔蒙路上。站在工作室楼下,心脏直突突,深呼吸好几下,努力喘匀了气,摸了摸兜里的枪,这才慢慢走进公寓大楼。我上到二楼,站在门口,直接把手枪掏出来攥在手里,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一点动静没有。我一脚把房门踹开, 透过月光,隐约看到对面有个人冲了过来,这人手里拿着一把刀,挥刀就砍。我冲那人连开几枪,那人拿刀的手上下挥舞了几下,停在了半空。我确定开枪的方向是朝向他,他也没有躲闪,只一两米的距离,我的枪法不会打不着,可他依旧站着。我走向他,想凑近看一看,身子刚踏进门里,右手边突然又窜出一个人,我连忙蹲下,朝着右边又是连开两枪。我拿出手电筒,一束光打进了屋子里,屋里的场景让我开了眼。这屋子里像是摆了个罗汉阵,整个屋子里有五个假人,手里都拿着刀,码放布料的架子上,还有些联动的机关。在屋子本来放假人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真人,浑身是血,他旁边的窗户开着,看样子他是从窗户翻进来的,也没逃过机关暗算。我喊那个人,让他躲到工作台底下。那人稍稍回应了一下,费力地挪动身子,藏在了工作台下。我拿手电照向这些机关,尽量避免触发,慢慢拆解这些零件。终于接近到蜷在工作台下的那个人。这人不是旁人,是我在白天见到的那个穿棕西服跟踪我的“尾巴”。他的右胸下侧,插着一把剪刀,腿上和肩膀上都挨了刀。他的手里攥着我白天丢给陈德明的名片。我抓起工作台上的电话,打算报警,这人呼吸急促,小声地求我别报警,“我是个贼,见不得光,你要帮我离开这儿,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的事情,就发生在这屋里。”他说,在苏州河假人浮尸出现之前,他偷过这间屋子,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儿。“你得把我送到老北门,那有个大夫,能帮我治伤,你把我送过去,我就告诉你。”我简单处理了一下他身上的伤,还试着拔出扎在他胸口的剪刀,结果疼的他吱哇乱叫。我也就放弃了。就在我准备扶他出去的时候,手电光晃过一排货架,在布料的缝隙中,我看到一个人正盯着自己。我卯足了劲,踹了那个货架一脚,货架倒向墙边,布料稀里哗啦散了一地,一颗木头脑袋滚了出来,脑袋上贴了一张人皮脸,是陈德明。小偷一紧张,深吸了一口气,血沫子顺着嘴角开始往下流,肺里都是血,憋得他喘不上气,他就又连着大吸几口气,血涌上来的更多了。我看我是没办法一个人救他出去,朝着楼下喊,又开了两枪。楼下路过一个巡警,听到枪声赶忙上来查看情况。小偷送到医院抢救,我到巡捕房做了笔录,折腾完天已经亮了。警察搜查了工作室,认定那张人脸是陈德明,警察认定陈德明遇害,毕竟按常理讲,没有脸的人也活不下去。小偷在医院抢救了几天,缓了过来,录了口供,说了他为啥来这间屋子。这个贼在一个月前就偷过这间屋子,从里面顺走了两匹高档呢布料。那天他睬好点,刚进屋里,陈德明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他来不及逃走,就躲到墙角那一堆假人里。从假人的缝隙里往外看到的画面,他说现在想起来,腿肚子都直转筋。“那个陈老板拿着一把锯,一瘸一拐地走到工作台前面,挽起左腿的裤管,一下一下开始锯腿。一边锯,自己嘴里一边嘀咕,大概意思是让自己忍一忍吧。”
小偷说,陈老板锯断了自己的腿,然后不知道从哪儿拎出一桶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塞进了一个假人模特里。小偷交代,苏州河的事儿在街上刚一传开,他就想到肯定是这个家伙干的。小偷上一次来被吓得够呛,走的时候落下一个胭脂盒,他怕警察找到这个胭脂盒,顺藤摸瓜把他拎出来。“人家是老板,说句不知道就能搪塞过去,我是个贼,警察要是找到我,我怎么也说不清。”他这回来,是为了捡回这个日本妓女给他的小信物。这之后,我一度被认定为杀害陈德明的嫌疑人,在巡捕房关了几天,后来戴戴把我保释出来。陈家门口已经贴上了警察的封条,我用小刀轻轻揭开了封条,推门进屋。屋子里非常整洁,有收拾过的痕迹,衣柜里的衣服和一些书都不见了,看起来就像是主人出游,暂时离开家一样。我找到公寓的管理员打听李雪宁的下落,管理员跟我说,这两口子应该是出远门了,具体去哪儿就不知道了。连着几天,案子没有任何头绪,李雪宁人间蒸发,警方对陈德明之死的调查也毫无进展。我的梦魇症也越来越严重,时常从梦中惊醒,那个变成假人木偶的自己,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的意识要么是在木偶里,要么就是在追逐木偶的另一个“金木”身上。而控制木偶的人,从陈德明,换成了周天赐、艾良秋、简大悟。
一个个控制木偶的人,拽着我在梦里跑、跳、翻跟头,每当我想要反抗的时候,我的关节都会被控制木偶的线扯得生疼,甚至撕下一层皮,然后大叫着醒来。
第五天夜里,我又做噩梦。梦里我走进一个小镇,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迷路了。
我转了很久,总是回到一座石桥上。从桥上看出去,是白茫茫的雪覆盖的小镇,天空阴霾,好像夜晚随时降临。
远处传来惨叫声,我循着声音过去,看到两个穿西装的人扭打在一处,其中一个倒在地上,已经成了血葫芦。
两人看向我,他们长得一模一样,都是陈德明。其中一个从口袋里掏出剪刀,扎向另一个的喉咙。
我大喊一声,冲过去。这时,巷子对面也跑了一个人,穿着我的风衣,戴着我的眼镜。他就是我。
醒来时已经九点,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信。
是一笔钱,是李雪宁给我寄来的另一半调查费,还有一张便签,上面写道,她与丈夫已经回到了老家,感谢我这段时间的帮助。嘉善是一个离上海一百六十多里地的镇子,典型的江南乡镇。到了嘉善,我直奔当地邮政局,询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李雪宁。一个邮务员说他记得有这么一个女人,几天前来过这里,印象深刻是因为她穿着挺时髦,像是大城市来的。我问他这个女人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邮务员摇了摇头,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哎,你可以门口卖馄饨的阿伯,我记得那个女人走的时候,跟他说了好半天的话,他们可能认识。”邮务员说的阿伯,是个在邮政局对面的街边摆摊卖馄饨的白胡子老头,看模样有六十多岁。老伯听我描述完,问我是不是陈家媳妇,我一听有门儿,老伯不仅认识李雪宁,还认识陈德明一家。“我也是前几天才碰见她,他们陈家兄弟俩自从去了上海,都没有回来过。”“没错啊,大的叫陈德明,小的叫陈德亮,俩人是双胞胎,你问的不是大儿媳吗?”我赶忙打听陈家地址,老伯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我也没弄明白。最后我索性塞给老伯钱,拜托老伯带我去。听老伯说,陈德明的家不在嘉善县城,在下面的天凝镇,早先陈家家大业大,是做丝绸生意的,从祖父那一辈起,改作了裁缝,给嘉兴府做官衣也确有其事,做裁缝的手艺就这么延续下来了。后来等到了陈德明这一辈儿,仍然子承父业学做裁缝。陈德明是老大,一心想继承家业。但是,他却天生不是块好料,虽说学到了手艺,但技术平平,毫无惊人之处。老二陈德亮,比老大聪明,也比老大手艺好,透着股子灵巧劲,陈父也就教了他更多裁缝的手艺。奈何得过小儿麻痹,左腿落下了残疾,打小就受哥哥排挤。
陈父临终前,虽然喜爱陈德亮,但只能将家业传给陈德明。毕竟,干裁缝这行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身体。
陈德明去了上海,凭借八面玲珑的社交本事,也混出了点明堂。
陈德亮则留在老家,性情越来越孤僻,不爱跟人打交道,而是自己鼓捣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手巧,本身自己走动也不方便,就爱自己一个人坐那儿鼓捣,做个能动的小木人,做个小推车什么的。”后来陈家父母先后去世,哥哥回老家奔完丧,就把弟弟带走一起到上海发财,老管家就是这时候离开的陈家,陈家的院子也就空了。乌篷船在天凝镇的小码头靠了岸,我多给了船家一些钱,让他在这里等我。老管家要带我去陈家,我怕出危险,就让他待在船上等我。老管家不明就里,看我一再坚持,也只好作罢。走进镇子时,天已经黑透,我按照老伯给我的线路,穿街过巷,找到了陈家。宅子久无人居住,又疏于打理,大门门板的裂痕有一指宽,两扇门板都对不上,我敲了敲门,门没有闩。我一推开门,傻眼了,这厅里不止我一个“人”。大大小小十来个假人,假人的脸是平的,没有雕刻出来。我心头一紧,站住了脚步,生怕触发了什么机关,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确定没有陷阱。这些假人动作各异,有的坐在椅子上高谈阔论,有的站在旁边端茶倒水伺候着。就像是老管家口中那个人丁兴旺的陈家。会客厅里,花梨木的太师椅、顶梁的楠木柱子,都显出这家曾经的富贵。我小心翼翼地穿过木人们的聚会,走到厅后面的两扇门前,轻轻地推开了门。这是个小天井,院子里,一张大门板上,躺着一个女人,赤身裸体。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站在门板一侧,门板上还放着一件旗袍,男人正在给这个女人穿旗袍。女人是已经死了的李雪宁,男人是陈德明,或者该叫他弟弟的名字,陈德亮。陈德亮把那具尸体翻过来,又翻过去,这件旗袍却怎么也套不上去。听到有响动,他抬起头,看到了我,先是一愣,然后依旧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找到这里来了,我以为你会死在我的办公室的。”他说这话时,声音极其平静,脸上也没任何表情,“金先生,你坐下,歇一歇,我就知道是这个傻婆娘给你通风报信去了,不过我不怪她,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你等我把她的衣服穿好,再送她一程。”“那首诗怎么念,‘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最好骗的是这个女人,最难骗的也是这个女人。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对劲的时候,只有她相信我是她丈夫,等到我把所有人都骗过去的时候,没骗过她。”“您猜怎么着,她在床上看出我不对了,我是童男子呦,没碰过女人的,当然不知道怎么弄,不像我那个哥哥,整天不知道练手艺,就知道玩女人,这个傻婆娘还不知道。”陈德亮越说越激动,突然从木板上抽出一把剪刀。我大叫一声,想冲过去夺下剪刀,他却突然把尖刀对准自己的脖子。
他一句话不说,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剪刀尖已经扎进了脖子里。我放弃了靠近他的念头,退后了两步,他才慢慢把手放下,脖子上淌出一道血痕。他放下剪刀,又开始给李雪宁穿衣服,但明显动作越来越急躁。嘴里嘀咕着怎么就穿不上。他拿着剪刀,去裁衣服,想裁宽松了好穿,可还是穿不上,后来就在李雪宁的尸体上乱戳。本以为他会反抗,就没收着劲儿,我俩都失去了重心,砸在了石板上,他手上的剪刀飞出去老远。我上去摁着他脑袋往石板上磕了两下,又捡起木板上的皮尺,抽出来,绑住他两只手,才算制服他。陈德亮没来得及拿起剪刀冲着自己,自始至终,丝毫没有反抗。当他看到自己裁的旗袍怎么也穿不到死去的李雪宁身上时,他眼睛里的光就渐渐消失了。从天凝镇出来,我让老管家去给大奶奶李雪宁收尸入殓。陈德亮的精神状态让我担忧,我连夜送他去嘉善,到县城找警署报案。我押着陈德亮往回走,一路上他自言自语,说起了自己和哥哥陈德明的事儿。本以为哥哥带自己去上海,是带着他来发财,没成想一到上海,哥哥就把他关进了工作间的密室里,囚禁起来,让他裁衣服挣钱,陈德亮在那间小屋里,一待就是七年。哥哥出车祸的那段日子,弟弟被锁在了小屋里,十几天,靠着一点脏水和自己的尿活了下来。等再见到哥哥,弟弟起了杀心,他想杀了哥哥,自己代替他生活,自己也要吃香喝辣,娶媳妇过日子。等他杀死了哥哥,发现哥哥的腿已经截了,他也锯掉了自己的腿。他把他哥哥的尸体扔进了密室,为了防止发臭,他又把尸体的内脏掏出来,放进了一个木头假人里,他还套了一件做废的西服,为了不让木头散架。“我本想着过上我哥那样的生活,可我是个穷命,我过不起,我不会谈生意,不会跟外面的人说话,连个女人都不会日,我只会做衣服。”回到上海,我向巡捕房报案,我带着警察再次来到了陈德明的工作室,找了半天的功夫,最后还是找到公寓设计图,才找到了密室所在。
陈德明的尸体放在密室的一张工作台上,覆了一层厚厚的生石灰。在密室里,警察还找到了好几套西服和大衣,应该都是陈德亮给自己做的。
我想起那个贴着脸皮木人脑袋,或许,陈德亮太想看看完美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才把哥哥的脸皮剥下来,做一个逼真的模特。
坐船回嘉善的路上,陈德亮时不时地问我,“金先生,你杀过人吗?”他说一会儿自己的事,就唱一会儿歌,用家乡话唱着小调,还唱了几句荤段子,逗得船夫也跟他唱起来。快到嘉善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水面上泛起一层雾气,船夫不敢大意,专心地划着船桨。陈德亮也不唱了,也不说了,他安静了好一会儿,转过头对我说,“金先生,我看得出你想杀了我,可你又不愿杀了我,为什么呢?”说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身子一仰,栽进了水里,水面上溅起的波纹,很快又被薄雾覆盖。
这是个关于「残缺」的故事。
陈氏兄弟,一个缺少机敏的天赋,一个缺少健全的身体。两人都追求完美,希望对方来补全自己。
但所谓完美,本是一个极端的想象。记得有个艺术大师说,不要试图追求完美,因为那玩意儿根本不存在。
世间所有的人,都是残缺不全的。痴迷完美的偏执,难免引来痛苦,若不堪承受这痛苦,那何必执着于完美?
老大为求完美绑架弟弟做奴隶,老二为求完美,需要杀掉哥哥。
最尴尬的是,本是要取代哥哥,享受一个「成功者」的快乐,却不得不先锯掉自己的腿,模仿另一种残缺。
除此之外,太爷爷金木的噩梦比故事更让我难忘。
或许,这个与正邪黑白混沌纠缠半生的夜行者,极力想压抑的某些东西,正是他如影随形的残缺,如月之暗面。
或许,执着于完美的幻想,不如接纳残缺的自己。
本文属于虚构,文中图片视频均来自网络,与内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