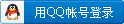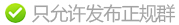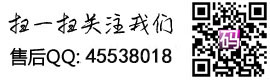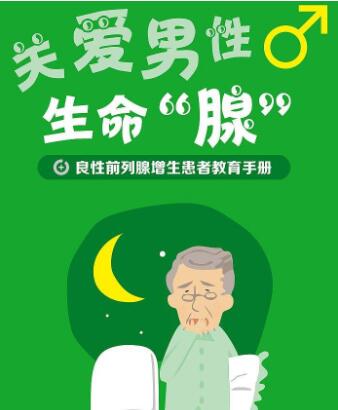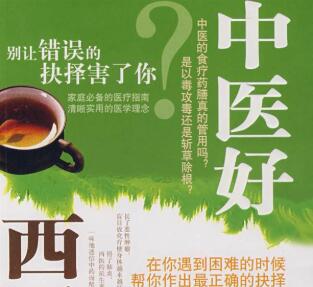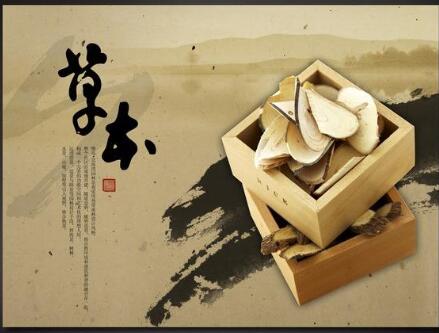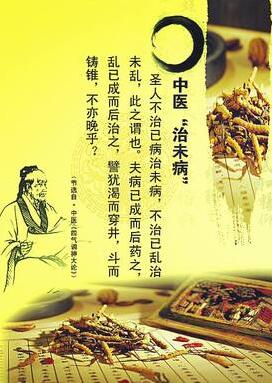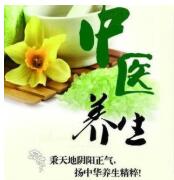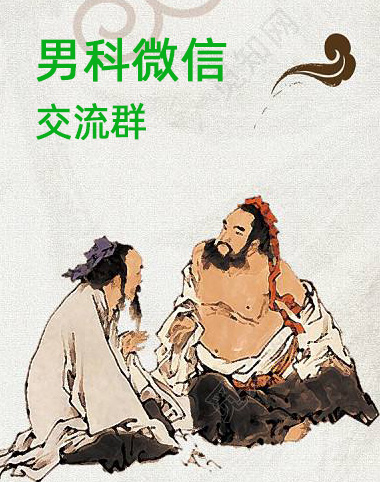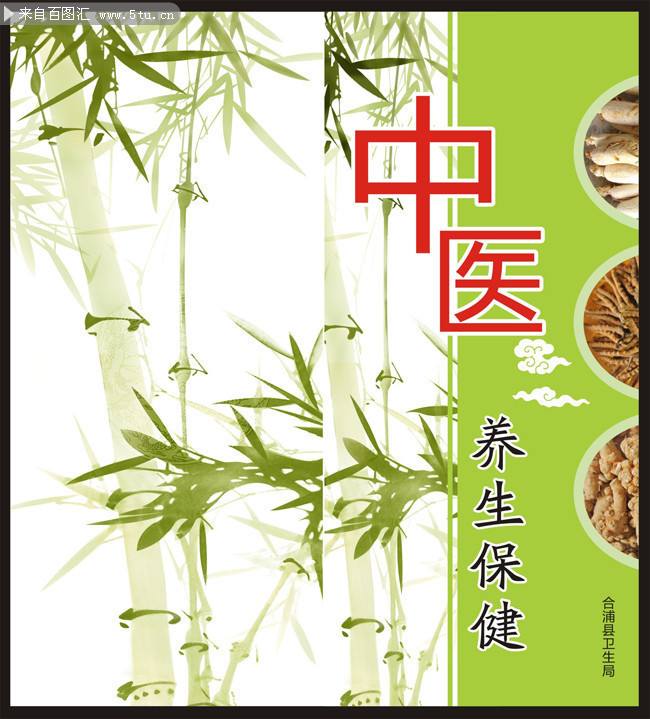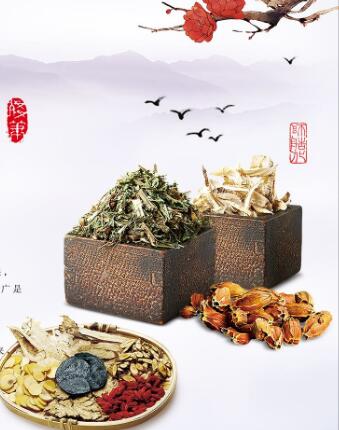“我想为女儿找一个老家的相亲微信群,在广东这边工作的。”53岁的刘梅还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她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打着,和手机另一头的陌生人交流彼此子女的信息。

女儿去年研究生毕业独自到惠州工作后,她的婚姻大事正式列上了刘梅的日程相亲微信群。为了让女儿早日“脱单”,她一方面积极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方面,注册了QQ和微信,加入了各种父母相亲群,下载了相关的APP,努力适应社交新模式。

母亲刘梅的心态并不是孤例相亲微信群。广州天河公园、深圳莲花山、上海人民公园……家长们扎堆替儿女相亲。
婚姻的围墙之外相亲微信群,超过2亿的单身人群及其背后的家庭组成了庞大的相亲市场(数据来自2016年国家年鉴),家长在各类相亲市场中奔忙,折射着中国式的婚姻焦虑。
相亲角搬到了网上
“看微信、看头条、看大亲家相亲微信群,每天都要打开无数次。”刘梅向羊城晚报记者展示了她目前最常用的三款手机应用,除了浏览资讯,她在女儿的婚恋问题上倾注了绝大部分的心思。
在今年9月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刘梅被推荐了一款名为“大亲家”的APP,“他们说有很多家长在上面注册了,都是给儿女找对象的,会根据你的资料和需求进行匹配相亲微信群。”
在此之前相亲微信群,她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陆续给女儿介绍了几个适龄男孩子,还第一次加入了QQ群,和在相亲角上认识的家长们互相交流信息,“我们以前落伍啦,现在互联网上信息好多。”
这些针对适婚男女家长的APP并不是新事物。早前,一款名为“人民广场相亲角”的APP因其颇具辨识度的名字,在上海的家长圈中火爆一时相亲微信群;另一款基于家长地理位置的相亲社交APP“亲家”,同样宣称着眼于扩大家长社交面,从而帮助孩子找到对象。
抱着不放过一丝机会的心态相亲微信群,刘梅下载了APP,填写了女儿的信息,没多久就收到了感兴趣家长送来的玫瑰和“点赞”。
“一般看到资料差不多的就会聊一聊。”刘梅并不熟悉互联网上的“套路”,她谨慎地开始了网上的交流,从常规的互相询问子女身高相亲微信群、学历、工作情况,到交流家里的经济情况,“有遇到过合意的,加了微信,还没线下见面。”
其实相亲微信群,她还在观望之中——“互联网上什么人都有,上传的资料并不一定真实”。她做了用户认证,也只和认证用户慢慢沟通,“父母登记的真实性相对比较高,但有没有诚意找,聊久了才能知道。”
在这个平台上,家长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后,会相互交谈试探,通过网络让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再交换子女们的QQ、微信等联系方式,由子女们决定是否见面,继而进一步发展相亲微信群。
中国式焦虑遇上互联网
“升官没有相亲微信群?”
“还没呢相亲微信群。”
类似的对话在QQ群“上海父母相亲会”里几乎每天都有相亲微信群,有意思的是,他们口中的“升官”并不是担任领导职务,而是升任婆婆、丈母娘。
这个210人的大群创建于2014年,常年在线人数达100人,每天活跃人员也有数十人。在该群公告里,建群的初衷一览无遗:“家长与未来的女婿相亲微信群、儿媳群内直接沟通交流,为忙于学习工作圈子狭小的孩子牵线搭桥,提供信息(孩子是80后90后单身青年)。”
在这个群里,家长们定期交流自家孩子的情况,顺便互相打听有无合适的资源相亲微信群。家长们都把群名片自觉修改成“省份简称 昵称 子女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在聊天时这些信息一目了然,越活跃的家长曝光度越高。羊城晚报记者简单统计发现,这个群里聚集了来自沪、皖、豫、苏等17个省、直辖市的家长,孩子年龄从1983年到1995年不等,多数集中在1990年前后。
“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姻的走向是中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相亲微信群。”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曾于2007年深入研究白发相亲角现象,并著有《谁来娶我的女儿?》一书。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在蔓延,“谁来娶我的女儿?”这样的呼号体现的正是这些公园相亲角多数父母的失望和无助,“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焦虑’。”
在移动互联网兴起前,家长为儿女寻找对象一般是通过熟人介绍,或者通过线下婚介所相亲微信群、城市公园相亲角等线下聚集地去收集婚配对象信息。而如今,这种“中国式焦虑”有了更深刻的互联网 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