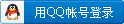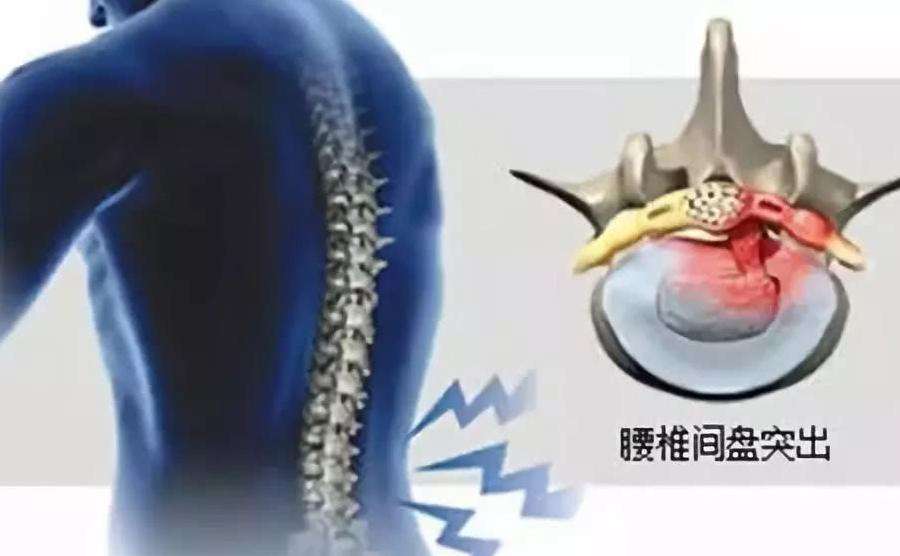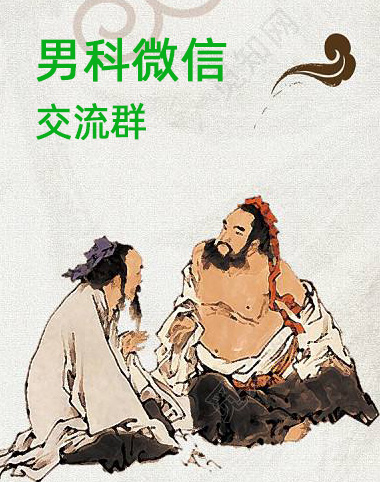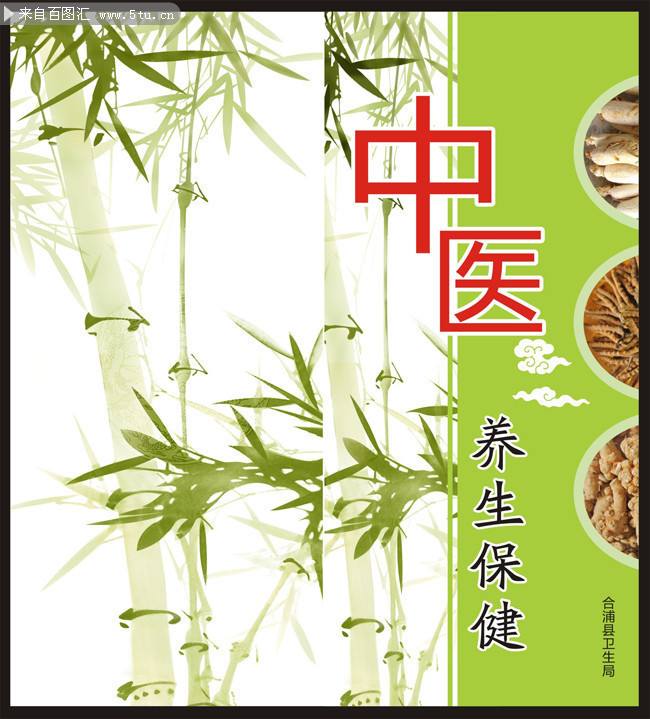精神病院,北京, 一九八九年,吕楠 摄
2005年作品统一用吕楠这名字之前,他曾用过马小虎、李小明等看上去无所谓的名字。
在他看来,每一部作品做完之后就与自己无关了,一个人跟他的作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消灭自我。我只是去歧义,去遮蔽,让事物本身说话,我只是起到一个通道的作用。”
他用15年时间完成三部曲《被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只能把我所有的精力、体力、财力投入到一件事情上,把这一件事做好。即便我集中了所有的力量,我还是做得这么艰苦。”
对自己重要的书,马丁·布伯《我与你》、《歌德谈话录》等,他看了都上百遍——听上去,近乎“疯狂”。
偏爱摄影的读者朋友,大多知道吕楠及其作品,可能如理想君一样,充满敬意。他以作品成就名声。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谈及对“名利”的感受:“以前我傻乎乎的,名利来了我还拒绝,我现在不拒绝名利,但我不会去追逐名利,但如果名利不给我什么,那么我还是继续做我自己的事,它影响不了我。”
今天的文章,来自陈丹青影像评论的首次结集《影像杂谈》。来来回回翻这本小书,最后选取有关吕楠作品的评论——尽管小书最后部分收录陈丹青的“私家摄影”,有意思,让人看到他的柔软。为什么选取吕楠作品,因为纯粹、孤绝,而这正是摄影所需要的。
无 言 的 劝 告
文/陈丹青
精神病院,北京, 一九八九年,吕楠 摄
精神病院,北京,一九八九年,吕楠 摄
精神病院,天津,一九八九年,吕楠 摄
在院墙内转圈环步的人群不能没有居中的那位仰躺者;六位玩牌的病人,顶在头上的白枕正好是三枚;乒乓球桌的围观者有三位举臂欢呼,在三副双拳的高低错落间,我又见到“大师意识”。
此外,人物的坐站、正斜、居中、靠边、二比二、一比三,以及在其他类似构成中,吕楠的苦刑——也即他的狂喜——如同卡蒂埃-布勒松给出的谜:我们永远不能解答这些局面的判断、捕捉是属人为抑或天意?出于耐心还是决断?这谜底,若以理论词语推断,乃因作者善于将“必然”强行制服于“偶然”,且本领深藏,置身事外。
精神病院,四川,一九九〇年,吕楠 摄
卡蒂埃-布勒松惯常顾左右而言他,但仍然声称:“我不关心其他,除了形式。”所有苛求于构图的摄影家均难摆脱卡蒂埃-布勒松式的影响,吕楠的功力却并非超人的机敏,反倒出于三分笨拙,以及,超常的忍耐—同样是抢救瞬间,他不属于卡帕一路,卡帕以“事件”为性命,无暇分神于校正景物边框线—吕楠则将视像通常置于均衡端正的水准,尽可能以日常而平等的视线观看对象(一如小津安二郎架设机位的谦逊意识)。极微妙的,我从中窥见柯特兹般的体贴,这体贴的可读性来自人性还是艺术性?
我无意将吕楠与大师相并列,他从来与浅薄的“洋味”与“现代性”划清界限:他懂得“形式”不是表象,而是对主题的全部了解,唯其如此,本土题旨才能见骨肉、有血性。这时,我们或许可以偏离形式,略微谈论吕楠的慈悲心。
精神病院,天津,一九八九年,吕楠 摄
瞩目于卑微的人群,探寻社会真相,吕楠是这类摄影众多介入者之一。但我们都会同意,仅只可数几位中国摄影家具有经典性的概念,吕楠无疑是其中翘楚。他从“宗教系列”、“精神病院系列”到“西藏系列”,呈现漫长而清晰的自我陈述,丰实厚重,气质深沉。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通常具有如下品格:沉潜、耐苦、同情心、宗教感、自我放逐……那是可能试炼的,但并不必定换取作品的经典性。
据说吕楠常年在藏区游荡,伴随歌德的读本与巴赫的音乐,我看他“西藏系列”,他于绘画图式的认知涵括过去数百年的欧洲经典,并深知绘画画面的完满性与摄影瞬间的凝固,意味着什么。要之,他并非在摄影时才是一位摄影家。精神病人与藏民在他镜头前不只是人性的对象,而是中介,与他自己一起迎向他追念的境界。那境界与他所见无关,除非进入影像,成为切片、构图,也即所谓“形式”,否则难以安顿所谓悲悯与良知——我指的是:摄影的良知。
精神病院,天津,一九八九年,吕楠 摄
这良知构成经典的稀有时刻,包括影像主体的“伴奏”与“复调”。吕楠专擅人物摄影,尤其是二三人一组的群像,但他在空无与物件中也能处处看见“人”:在几幅孤单病患的动人作品中,使他心惊的不只是面目神态,更兼无情的“周围”——空床破败、甬道浊暗、被抛弃的工地、绝望的墙(那位不知何故进入病院的美术教师身后,贴着他描绘的“雷锋”),在纠缠于后园荒草的两位疯子头上,吕楠摄入晴空和云,我们的目光于是被带出墙外的“人间”……
这是一组不忍卒睹的影像,重重封闭的空间令人窒息,所有病患苟活着,生不如死。这悲惨景象被如此“艺术地”拍成照片而竟免于罪过,实在因为作者无比善良。奇异的是,笼罩其间的非人氛围被赋予一种介于死活之间的存在的庄严。
精神病院,云南,一九九〇年,吕楠 摄
我忽然明白这些照片难以阻止我们的遗忘,它们成为照片,其实不是为了丧失理智的精神病人,而是一份再恳切不过的劝告——请好好活着吧,戒除种种不安与罪孽,因为你们健康,正常,没有疯。这无言的劝告来自吕楠的作品,而不是病院中那一个个不幸的人。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影像杂谈》
陈丹青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陈丹青影像评论的首次结集,并配以作者的手机快照。《影像杂谈》以画家之眼,谈论时间对于摄影的参与,记忆对于影像的介入。作者犀利的视觉经验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一张照片的平易切口。
每幅图片,都有一段详尽或确凿的文字说明,介于图像与文字之间的隐形距离,得以形成抽象的概念、真相与想象,而作者的文字,收放如锚。
陈丹青《影像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