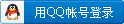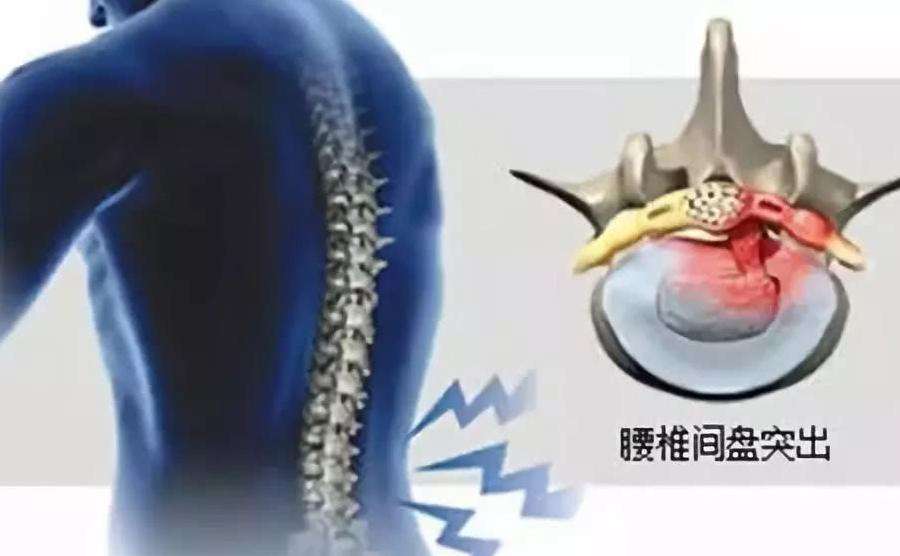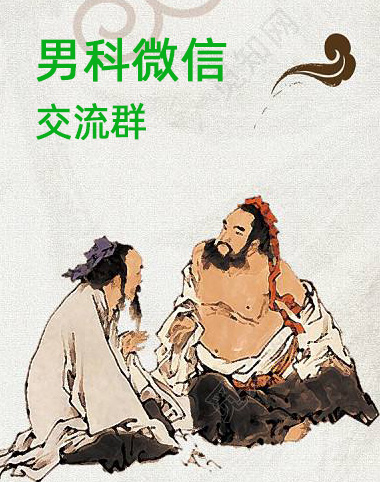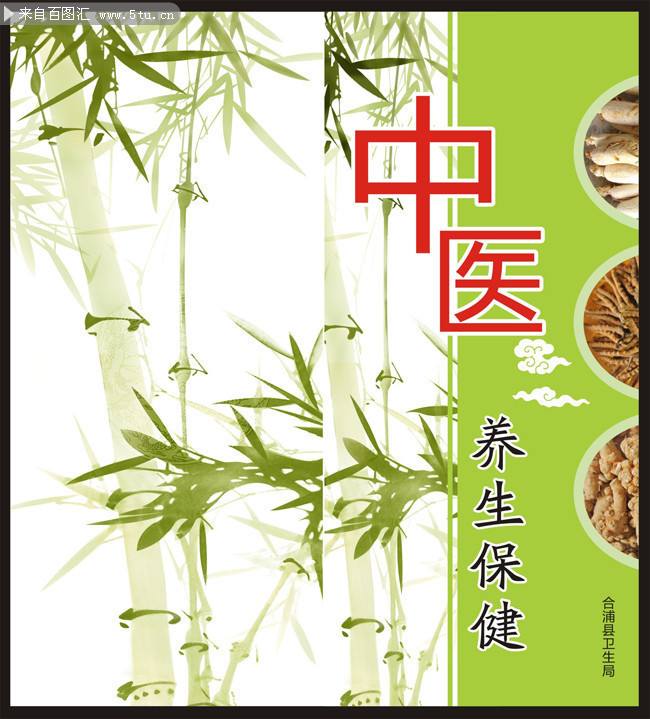文|谢梦遥
编辑|金石
「男人还有底线呢?」笑果文化的脱口秀演员杨笠说出这句话后,一场战争在互联网上开启了。话题一度占据热搜榜首。
表面上看来,这是某些因这句话被触怒的男人们,与杨笠的辩护者之间的战争。除了在社交媒体互相嘲讽或者激辩,还有人甚至发起了举报,指称杨笠「制造性别对立」。这场战争也延伸到女权等其他议题上。
但这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在公共人物中,几乎看不到杨笠的公开反对者——国际关系学院法学教授储殷可能是少有例外,笑果曾经的签约艺人池子在表达语焉不详的嘲讽后很快噤声了。姚晨、黄西、苏醒等人对杨笠予以声援。这毕竟是一个属于娱乐圈的话题,没有得到媒体的全方位跟进,但提及此事的主流媒体普遍对杨笠持支持或宽容态度。
失去语境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那句话往前追溯,是杨笠与男性密友的一段打趣对话。更大范围来看,这句话在是一种由单人手持麦克风进行的引人发笑的表演(即脱口秀,或称单口喜剧)里,作为某个笑话的最后一句(即梗,或者包袱)而存在的。从现场效果来看,它成功完成了梗的作用。
在一片喧嚣中,杨笠和笑果文化均保持沉默。
杨笠在《脱口秀反跨年》中调侃男性图源网络
把杨笠当成一个捍卫女性权益的顽强斗士完全是一种误会。在《脱口秀大会3》,她表现优异杀入决赛,她说出的「为什么有些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成为破圈金句。但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她没有顺应一般期待,对于女性议题进行更深入论述,主张什么或者批判什么,而是把价值判断收了起来。她的脱口秀里,除去看似凌厉的调侃,不难找到柔软的部分。她承认有她对恋爱的向往,也讲述独自接受手术的卑微感受——更多时候,她不过是讲述个人的故事。
从这一点上,她没有变过。早在几年前在与《人物》的交流中,她就表示不愿被划入女权群体,对此也没有体系化的思考。那时,她是脱口秀厂牌「单立人」的签约演员,入行仅一年,台风却和如今非常接近。她身上有一种笃定的气质,使用一种淡淡的不在乎的腔调。她承认她主动模仿美籍脱口秀演员黄阿丽。那时,她的段子尺度比现在劲爆得多。在一场演出里,她讲了一个女性如何在洗澡时站着撒尿的段子——用同为脱口秀演员的刘旸的话说,「有一种野生女权的味道」。杨笠把解读的权力留给观众,最重要的是,「当别人笑了,我就觉得我得到赦免了」。
那次对话在2018年7月进行。杨笠与《人物》谈及家庭、女性演员的优劣势以及对黄阿丽的模仿。
以下为杨笠自述。
我们家是大家庭,跟爷爷奶奶住一起。在我们家吃饭,我爷爷有专属位置,上菜的是女人,我们家女人就自动把这个位置当成最好的位置。后来就是我爸。我爸坐那个位置,他不来,都没有人坐。我爸是比较沉默寡言,坐在那边,他都不用说话,真的所有人就会自动替他弄好。我奶奶就会自然地把菜都放在我爸一边。有一次我就故意让我妈坐,我妈就坐下了,我爸来了以后,就在那儿站着看着我妈,我妈就起来了。
我妈脾气很好,她从来不指责我爸。但我从小心思比较细腻,内心跟我爸的冲突很严重。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写作文,写了一篇《爸爸的脸》,就是说我爸特别爱变脸。对他的那种不服,可能就是属于对男权的反抗。
各方面我都会挑战他。我还记得我大学没毕业的时候跟我爸说实习的事儿,我爸就说,你不管去哪个公司,你都要拼命给别人干,我说那不一定,那凭什么。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问题,进入社会以后,面对了很多事儿的时候回想起来,才和解。
说脱口秀后,我想讲关于我爸的事儿,我最先想到的梗是我妈负责家里所有事儿,我爸只用做一件事儿——就是做自己。然后往前往后写了一堆,那是我的第一个版本。因为太暗黑了,效果一直都不是很好。当时一直有人跟我说,观众都不笑是因为你对你爸太狠了,大家没有觉得他对你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你反倒一直在指责父母。所以我就只能想办法改。
后来换了一个版本,技巧各方面都有一些成长,效果就比原来好了一些。我是觉得,一个事儿你必须和解了以后,才能讲好。你只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讲不好的。
为什么我跟他们和解了,因为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还有这些不满意,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伤害过我。如果他们真的从小就打压我的话,我是不会有勇气的。我能意识到他们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我好,我才会有这么多抱怨、罗里吧嗦的话。
我爸我妈是很实在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概念,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我是不是开放、是不是多元化的概念,就没有。我们家完全没有城市生活经验。
辞职说脱口秀的事,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爸跟我说,你一年以内能上台吗?我说可以,我爸说给我一年时间让我去试。
我还问过周奇墨,他不是上电视(讲过)嘛。我说你讲你爸那些事,你爸会难过吗?他说不会,他会觉得这个事儿跟他有关,但是你得把观众讲笑,观众笑了,他就不会难过了。
杨笠在《脱口秀大会》上走红的段子图源网络
说脱口秀之前,我干过很多工作。我原来是学设计的,做过半年设计。我设计做得非常差,我就辞职,当时处在崩溃状态。我想怎么办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我心气又高,我想那我就做一个我能做的事儿。正好当时我住的旁边有一个剧场,我很喜欢话剧、电影什么的,我就去做了一年的检票的场务。
我在当场务的时候,看过大山讲脱口秀,他办个专场。石老板(「单立人」创始人)他们去开场,我完全不知道是谁。我们检完票靠在门上,我同事看着说,啥破玩意儿。一个原因是,观众不投入,都是一些老大爷,不是脱口秀观众,本身就听不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对我们外行人来说,在一个正规的剧场里,这个表演太轻量了,不那么丰富,会觉得特别抽离。
那时候完全没吸引我,没想到半年以后我就成了脱口秀演员。
一步步走到这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实话最开始我上台,就是想在我最怀疑自己表达能力的时候,在陌生人面前表达一回而已。那天讲了一些段子也不很好笑,没有想到我讲了以后,突然有一种好想继续讲下去的感觉。这种感觉好好啊!
我第一次上台应该是2021年5月底,在北脱(北京脱口秀俱乐部)那边讲。我写的第一套东西就是一段话,没有梗,也不知道怎么加梗。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讲这段话,虽然它没有梗,但是我还是从这儿去挖掘。我没有考虑过喜剧天赋的事,支撑我进这行的,是表达欲。我最害怕的是我没有表达欲。当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表达欲的时候,我就没有上台的激情了。
后来在家看专场,看《手把手教你说脱口秀》,自己憋了几周,写了一些转折的东西,都是那种预期违背的,还是不好笑。直到有一天我问周奇墨,是因为我太不好笑了吗?这是一个特别笼统的问题,因为我根本就毫无头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好笑。他说,可能是缺少夸张和修辞。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大概知道我的文本要往哪方面走,才写出了一些段子。
当你要表达,是需要你对生活的观察去填充的。比如说你要向观众形容伤心是一种什么感觉,你不能只说我很伤心,你要用一种观众能理解的东西,让他去理解你的伤心。我没有任何(创作)规则。一个东西是我想说的吧,有灵感,我就往前写一点,往后写一点。往前写就是写前提,你以什么角度告诉别人。往后写就发展,比如说设想一个场景,运用混合技巧。
我一开始说话就慢,大家是以为我很淡定,其实是因为我紧张加词不熟,导致我语气想很有波澜都没有什么。所以有一阵,当我词熟了以后,我的节奏又变了,反倒不如原来不熟的时候了。
黄阿丽有一阵在网上很火,她的专场我看过很多遍了,怎么也得有十几遍吧。她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属一属二大的。我觉得她节奏特别好,我跟她学过,表情也是有意识地模仿。如果她讲了,我觉得好笑,我会暂停,自己讲一遍,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那个节奏。
说实话,我一开始觉得女性做单口是优势,因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上台有自己的标签,女演员是自带标签的。我在台上的形象一直就是单身、特别想谈恋爱、特别不讲究的那种女生。
但是讲着讲着,我发现观众在期待女演员的时候,其实他期待的就是两性内容。女演员上台你就是坏人,你是坏人所以才会笑。劣势就是在这儿,你讲别的时候他就有点走神儿了,当然也跟你能力有关。也有可能是我还没有做得那么好。
我做演出,主持人说怎么介绍我,我就说,要不你就说我是个女演员吧。那个主持人就会下意识说一句,这个也太性别主义了吧。每一场演出,我不断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是说我另要立一个标签,是女性这个标签太显眼了,是你避不掉的。你必须要学会处理它,不管你是正面地去迎接它,还是你躲避它。你要想清楚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每一个演员都有劣势、优势,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你能做的就是想办法。
国外脱口秀演员里,我喜欢路易CK,他会去思考很多别人不思考的事情。他作为一个白人,讲黑人。他频繁地讲恋童癖的问题,这个在国外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不能踩的线,但是他愿意去解读。我最喜欢他身上的一点是,不要用带着既定的观念和标签去看一件事,这也是我希望我能做到的。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事儿,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人和人的关系,不要带着标签去看。
我受过一个打击,有一次开放麦,我讲的是我去夜店那个段子,要演放得开的那种女生的状态嘛。坐前排有两个穿衬衫和马甲的男观众,喝着酒,有点醉了,下意识说了一句,「好骚啊。」这个事对我是一个打击。因为我下一个段子正好要讲那种特别猥琐的男人,我就顺便指了一下,我说「就像这位观众一样」。
虽然我当时怼回去了,但是你又觉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你不能是上纲上线的。因为你本身做这个工作,你就会冒犯很多人,你不希望别人上纲上线。你自己也不能,你必须得是最开放的那一个,因为这一行就是这样。
经过这个事儿我才意识到,女生讲一些大尺度的段子,是需要心理建设的。原来不用特意去建设,表达欲已经支撑我去讲这个事儿了,但当他出来挑战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需要建设的——我必须得明确地知道,我不是在利用这件事哗众取宠。我讲这个事儿,是因为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才能继续讲下去。
我对女权概念什么的,是很懵懂的。开始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别人说我是女权。因为这个事我不懂,我就要站在其中,我就觉得很危险。而且我觉得你主张什么,你被划入一个群体,如果这个群体干了什么傻事儿,就会有人用这个来绑架你,你也会受连累。我不愿意站在一个什么群体里,尤其是一个我不了解的群体。
我的目的是想让大家自己去思考这个事儿就好了,我不想传输一个观点。比如说身材那个段子,「男人越喜欢什么我越不长什么」。其实我可以讲观点,可以讲说女人为什么要去讨好男人,为什么要为男人改变自己,我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最起码我不愿意讲。
我真的最怕别人点头,别人给我点头我就慌了。我不想让观众来觉得我听到了一个什么对的道理,听到一个好笑的事儿就行了。我不想说教,因为要负责任。当你真的是改变别人或者说教别人的时候,你要对这个事儿负责任的。
我就是凭感觉写段子。我权衡过,是按《手把手教你说脱口秀》那样的方法写段子,还是我想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尽量让它好笑就好了。我发现,如果我抛弃我想讲的东西的话,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吗。
我的东西不是黄段子,不是指向色情的,它是指向一种大尺度的语言。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说别人不喜欢听的话的人。你拿话去刺别人,别人那个反应会让我觉得刺激。当别人笑了,我就觉得我得到赦免了,我有一种成就感。别人不笑,我也有一些收获。
作为一个女演员,我一直要不断去权衡段子里的冒犯性。你要分析自己,失败是为什么,是我能力没达到造成的不好笑,还是因为冒犯性,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取舍。到现在我也有很多摇摆不定。你上台骂人肯定是会受到反感的。喜剧是需要角度的,它不是一个事儿,你「嘎嘎」说就好笑。脱口秀演员要学会去找那个角度。
这里是「坏姐姐来了」,一个女性成员占据绝大多数的团队。社会对于女性的凝视已经让我们非常烦躁,我们相信女性是充满生命力的,有多样可能的,而不是凝固在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之中。
我们将在流行文化的流变史中观察女性,关注女性情感、思想、境遇与生活,去表达女性的见解与声音。她们可以时髦,也可以疲惫,可以美好,也可以狼狈,她们可以非常有力量,当然,也有权利十分软弱。
她们不会被大众审美所绑架,坏姐姐永远都对。
扫码关注公众号「坏姐姐来了」
星标关注《人物》微信公号
精彩故事永不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