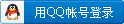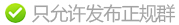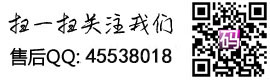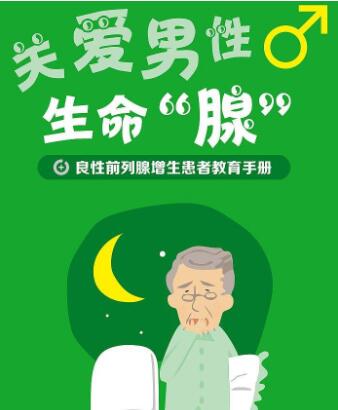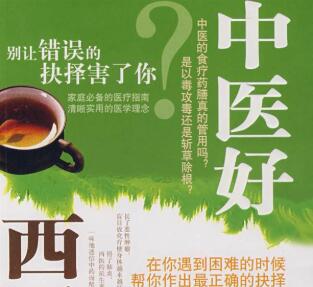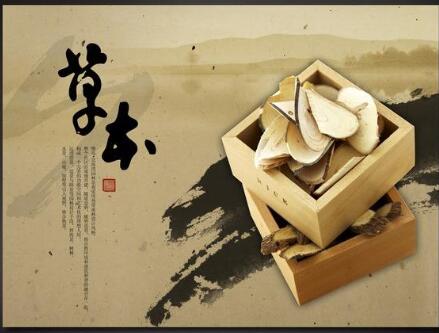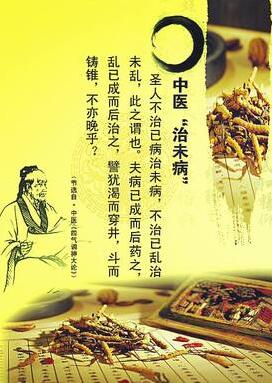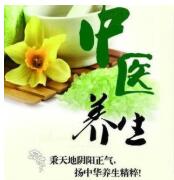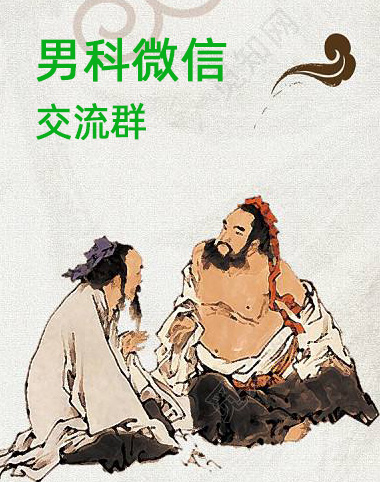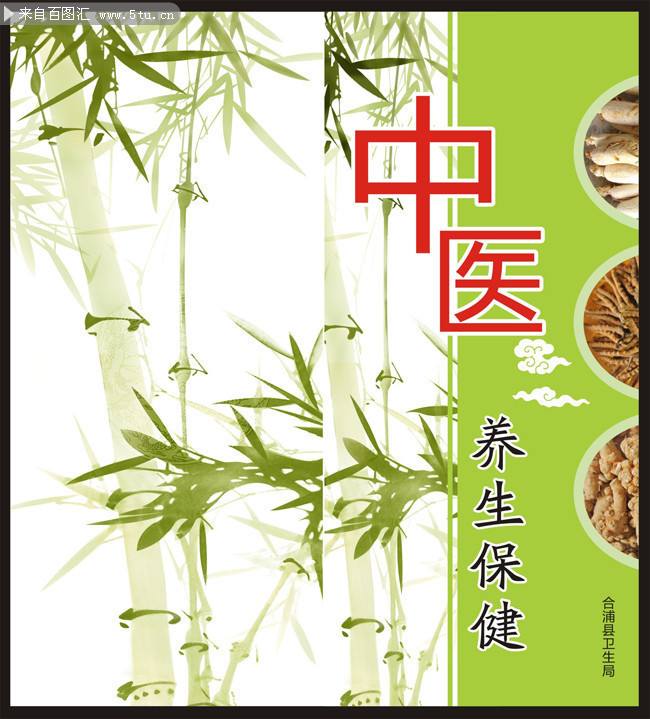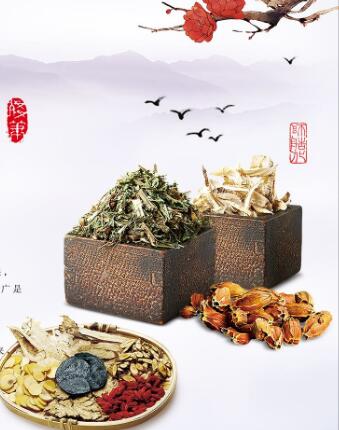如图,这篇文章主要讲这个
前段时间张艺谋的电影《最冷的枪》已经立项通过并且开拍,随着管虎、郭帆的《金刚川》的上映,国内掀起纪念抗美援朝那段光荣历史的浪潮,各种电影也是纷纷上马。先是张艺谋的《最冷的枪》,紧接着就是徐克、陈凯歌、林超贤的《长津湖》,大导演们纷纷拍起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
其中《最冷的枪》的故事梗概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狙击手张大弓枪法过人。美军倾尽全力欲将之消灭。面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张大弓临危不惧,同敌人展开周旋,最终扭转战局,成功击败对手。
影片以志愿军狙神张桃芳为原型,因此最近也出现了很多介绍张桃芳英勇事迹的科普文章。但实际上,张桃芳背后的那段历史,要远比单纯的个人英雄事迹复杂的多。而且狙击英雄也不止他一个,他只是那个特殊时期中的典型之一。
岂能让你们如此嚣张
1951年6月以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战线相对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基本战法可概括为“坚固坑道体系防御战”,主要思想是:以“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为指导,采取以阵地战为主,与阵前反击和狙击相结合的方式,在后方强大炮火支援下,依托坚固坑道体系,实行阵前反击、小包围、小歼灭战的“零敲牛皮糖”战术,达成迫敌和谈的战略目的。
鉴于美国谋求“光荣的停战”,表示愿意谈判,双方开始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漫长谈判历程。
1951年8月中旬,志愿军三八线附近的第一线阵地——西起土城里,经松岳山、五里亭、平康、登大里、艾幕洞、西希里、沙泉里至东海岸高城,全长250余公里的防御工事全部构筑完毕。
▲战士们称自己所筑的坑道为“无敌坑道”。
经过一年多的惨烈厮杀,朝鲜战场逐渐归于平静。然而平静之下,实则暗流汹涌。
美军在朝鲜战场打了一年多,投入的总兵力已达数十万人,并且拥有绝对的装备优势,但却只打出了个看不到任何胜利希望的僵局,实在是有损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面子。
而在三八线附近,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阵地平均距离400-500米,最近处仅有100多米。有志愿军战士对此的描述颇为形象:“对面阵地上的美国佬,眼睛是黄的还是蓝的,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种长期对峙的阵地战,对装备劣势明显,炮兵火力密度和射程不占优势,有没有制空权的的志愿军来说极为不利。当时,美军1个军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超过1400余门,志愿军1个军仅有各种火炮198门。
阵地战之初,吃过志愿军大亏的美军,泄愤一样的向我军阵地倾泻炮弹。不仅大炮昼夜炮击我阵地,坦克也嚣张地开到前沿阵地,肆意射击。平均每天向我重点阵地发射2000余发炮弹。地面部队也仗着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公然把警戒阵地不断往志愿军阵地前挤,甚至修到了志愿军的眼皮子底下,前边的两军阵地最近相隔100米就是这么来的。
▲上甘岭阵地。
美军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当然也是为了谈判桌上能占到更多便宜。
而此时的志愿军阵地,基本上还是野战工事,还没有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阵地上防御设施简陋,难以抵御美军密集炮火的轰击。再加上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落后太多,又缺乏制空权,火力不足的后果那是相当严重,志愿军战士们只能憋屈地窝在阵地上,被动挨炸。
因而在阵地战初期,白天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美军手中。美军车辆、人员在志愿军面前肆无忌惮地频繁活动。只要天一亮,无法忍受枯燥乏味阵地生活的美国大兵们便出来撒欢了,跳舞、喝酒、晒太阳、摔跤、洗澡……反正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志愿军官兵们怎么能咽的下这口恶气。然而却又无可奈何,常常就是只要志愿军对着嚣张的根本不想隐蔽的美军一开火,马上就会招致美军疯狂的火力报复。大炮和飞机轮番轰炸,每到这时,美国大兵还不忘站在阵地前看热闹,对着志愿军阵地手舞足蹈,大喊大叫。
▲还有可乐喝
为避免招致无谓损失,部队一度给前沿部队规定了不主动惹事的戒律,把“不随意开枪”作为了一条纪律。
一味忍让也不是志愿军的风格,蛮干不行,只能智取,这也一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既然不能与美军拼消耗,那就必须在战术手段上下功夫,于是志愿军提出了“变死阵地为血脉流通的活阵地”的口号,狙击活动应运而生。
既然双方阵地的距离那么近,已经进入了各种轻武器的射程,所以虽然志愿军部队没有真正的狙击步枪,但同样可以靠着步枪、机枪射杀敌军阵地上的目标。
到底是哪位英雄破例先开了第一枪?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始作俑者”是驻守黄鸡山前沿的第40军355团第9连副连长徐世祯。
1952年年初,徐世祯实在是看不惯对面阵地的英国兵嚣张的样子,于是光着膀子,浑身涂满黄泥,提着杆“水连珠”就出去了,然后就杀了7名敌人。徐世祯出了口恶气,本以为会被通报批评,没想到却等来了团里的通令嘉奖。
▲志愿军狙击手
而有详细记载的狙击战,也发生在1952年年初。当时驻守三八线中段金化地区的志愿军第26军230团率先组织全团特等射手开展冷枪运动。该团特等射手使用各种轻武器开展“打活靶”竞赛,用29发子弹毙伤敌军14人,吓得对面阵地上的敌军几天内没人敢在阵地上露面,狠狠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总部马上就把230团的经验向全体一线部队推广,并作出指示:在与敌对峙状态中,对敌之小群目标及一般目标,每日指定值班的轻重机枪不失时机地寻求射击,对于单个目标也应组织值班的特等射手专门寻求射击目标,这将给敌人甚大杀伤。
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坚决反对认为步枪在近代战争中已是落伍兵器的说法。
志愿军的冷枪冷炮运动拉开帷幕。
冷枪运动,英雄不止张桃芳
但冷枪冷炮运动在初期进展地并不顺利。因为1952年3月底之前,志愿军的阵地尚未巩固,以坑道为核心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正在构筑之中。
狙击作战,狙击手即使伪装得再好,枪声一响,位置也会暴露,美军的炮火也就随之而来。只要志愿军狙击手的位置一暴露,不到一分钟就会遭到报复性炮击。常常是志愿军的狙击手打死一个敌人,敌人就用炮火轰半天。
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护工事,志愿军狙击手伤亡较大,普遍产生了畏惧情绪,认为“冷枪冷炮是小打小闹”的观念也开始流行。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志愿军发挥军事民主的老传统,号召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一系列应对办法。
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合格狙击手,并不是单枪匹马去执行任务,而是分成2-3人的狙击小组,由组长带队进入狙击阵地。其中一人专门负责观察,射手则分布于周围隐蔽位置。发现目标后,观察员发出信号,射手立即开火,打完后,不管目标死活,立即转移。
战果由观察员最后审定。敌人被射倒后,有另外的敌人抬走或拖走的算死;背走架走算伤;射击后敌人倒下后又跑了则算活。这样,就尽可能地保证了战果统计的准确。
而对于狙击阵地的选择,基本要求是能够“有效地杀伤敌人和保护自己”,以防止狙击手开枪后遭到火力报复。位置一般选在敌人运动或运输人员往返的必经之路上,并避开我主阵地火力点和观察所,同时要求地势较高,可以俯瞰敌军阵地且射界开阔,以增大对敌之威胁与保证我阵地之安全。
▲张桃芳
工事构筑要求地势隐蔽、便于伪装,并造一至两个假阵地,迷惑敌人。同时每个狙击手应有两个以上预备狙击台,并在附近构筑防炮洞,以便在完成射击任务后,迅速转移位置,避开敌军火力报复。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志愿军的狙击手们还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周密侦察,分段、分点地予以编号,并一一进行了测距、试射。只要有目标出现,观察员只需报出目标所在区域的编号,射手迅即动作,根本无需长时间的瞄准,以致丧失战机。
正是因为狙击手们在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枪法也越来越纯熟,使得冷枪冷炮运动开展得越发顺利,逐步成为了朝鲜战场阵地对峙阶段志愿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张桃芳向同班战士传授经验
从志愿军某部狙击小组组长苏许松的关于一次狙击行动的日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志愿军狙击小组行动的基本面貌。
七月十三日 战士 苏许松
早上三点钟,排长把我喊醒了。我一面披带武器一面赶忙招呼上任炳清、郑应高,三个人走出了坑道。
天还黑得看不见东西,可路是熟的,我们连跑带窜地通过那片敌人炮兵封锁的固定区域,翻过一个小山包,就到了我们的“靶场”。这时天已黎明,站在立射工事里,对面敌人阵地上的地堡、交通沟、厕所,下面的公路、小河都一点一点清楚地显现出来。郑应高到防炮洞里去做早饭。我把枪检查好,架在射击台上,用松树枝伪装起来。任炳清拿着望远镜在掩体里替我观察目标。
不大一会儿,只听任炳清喊;“组长!注意一号”!我往地堡那边一看,一个大个子敌兵穿着衬衣、短裤,在地堡出口探着头,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然后,一溜烟跑进厕所去了。任炳清直催:“打呀,打呀”!我说:“别忙,总得让人家解完手呀”!
我把表尺定好,推上子弹,就瞄住从厕所到地堡中间的三号目标,等了足有三四分钟,那家伙才钻出来往回跑,我停住呼吸一扣扳机,任炳清喊了起来:“打中了!打中了”!我细看看这个敌人半天没爬动,就捡起一块石片,在身后的胸墙上添了一道。这是第四十一个。
待了一会儿,任炳清又喊:“注意!四号有三个敌人”!我朝河沟望去,三个家伙正在河边洗脸呢,任炳清指着当中那个说:“你看那个屁股上好像是支手枪,可能还是个军官哩”!我说:“那就先拿他开刀”!枪一响,任炳清说:“近了,打到河里了”!趁着敌兵们一怔神,站起来想跑的时候,我早修正好了距离,照着当中那个又一枪,这回他乖乖地躺到河沟里去了。剩下那两个紧挨在一起逃命。这正好打,我一连气打出了五发子弹,这两个也摔在河岸上不动了。任炳清跑过来一面替我画道道一面说:“今天早上一连气四个”!我说:“等着吧,还有拉尸的呢”!
敌人的排炮打来了,可我们已经进入防炮洞里吃早饭了。任炳清说:“这炮弹一股劲地落,敌人的报复性不小呀”!我听了一下,放下饭碗说:“不光是报复,可能是掩护抢尸首,走!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刚出洞口,就被落在附近的一颗重迫击炮弹盖了我满身土。我三步两步跳到工事里往前一看,果然,三个尸首都不见了,两个美国兵正抬着一个长包裹往回走呢。我照着前头那个打了三枪,后头那个丢开手拔腿跑进树丛里去了,算他腿快,这回只打上一个。
下午,我们潜伏到敌人阵地的侧面,伏在早先挖好的隐蔽工事里。敌人那边公路上开来一辆汽车,车子停在山脚下,三个敌人下车往山上爬。任炳清问我:“打吗”?我说:“等等,不到时候”。三个敌人爬到当中转弯的地方,一条线平列地对直我的枪口,我说:“先打后头那个,省的他爬山挨累”,只一枪就撂倒了。先头两个好像听到口令似地也同时卧倒了。我耐心地等着。好半天,第一个先把腿抬了一下,我没理他,接着他又把头抬了抬,我还不理他,后来他一只手撑着地面抬起头来,我估计他要跳起来跑,早把枪瞄准了,他刚一跃起,我的枪也响了,这个敌人滚了几步远,横在了山坡上。任炳清喊道:“打的好,来了个狗啃屎!你看那个四条腿爬呢”!我放下枪说:“这回不好打了,我看在小桥跟前等他吧”,果然,那个敌人爬了一阵,不见有人打他,就猛地往前一蹦,飞跑起来。跑到小桥跟前,脚步放慢了些,我抓住时机,用两发子弹又把他放倒在桥头上,便宜他多活了二十几分钟。
天色近黑了,敌人阵地上的探照灯也亮了,“壮胆枪炮”照例地四处乱打。让敌人去为他们的伙伴送葬去吧!我们三个人趁着黄昏走回了坑道。
——引自《志愿军一日》,志愿军一日编辑委员会编
颇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快意。任你狂轰滥炸,就是拿志愿军狙击手没办法。就是成百上千个这样的狙击小组,在三八线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也涌现出很多打死打伤敌人超过百名以上的狙击英雄。
其实张桃芳只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他个人的狙杀记录,居于全军第一。但他一共用了436发子弹,若要论狙击精度,还要数邹习祥。
▲新闻纪录片中,邹习祥在向战友传授经验。
邹习祥是贵州人,祖上都是猎户,自幼就随父辈到神山里去打猎,练就一手好枪法。19岁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邹习祥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踊跃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在上甘岭,他仅用了206发子弹,就狙杀了203名敌人,可以说几乎是百发百中。
张桃芳的同班战友吕长青,也曾“杀死杀伤敌人178名”。而且当时他和张桃芳共四个狙击手分成两班,轮流杀敌,张桃芳使用过的那把已经躺在军博展览的莫辛纳甘,他们都用过,毙敌无算。
就是这种神出鬼没的冷枪运动,一举扭转了阵地战的格局。志愿军狙击手们卧伏在山谷中、枯树洞里、岩石缝中,甚至潜伏到敌人的阵地鼻子下面,随时猎杀任何暴露的敌人。
昔日嚣张无比的美国大兵再也不敢在阵地上露头。不仅夜间戒备森严,白天也是死寂无人。官兵们整日龟缩在地堡和掩蔽部中不敢露头,连大小便也不敢出来,只能用罐头盒接着,然后随手向外一扔,搞得其阵地上臭气熏天。
朝鲜前线阵地对峙的主动权由此开始逐步转到了志愿军手中。
1952年5月底,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大规模筑城基本完成,在横亘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200多千米的正面构成了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
▲战士们打通坑道胜利"会师"
▲图书馆看书
▲包饺子
▲坑道真是无敌
有了更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冷枪冷炮运动开展地更加“肆无忌惮”,面对美军的龟缩战术,志愿军的狙击手们又开动脑筋,探索出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狙击作战战术手段。
比如,对敌一个阵地连打几天之后,要适当转换狙击目标,让敌人放松警惕;对乘汽车的敌人,要先瞄准其停车点,等车停下来,第一个人刚站起身时开枪,这样可以连续射击,击杀数人;对早晨外出解手的敌人,要等其蹲下时再开枪,这样一枪不中还能开第二枪;对洗澡的敌军,要在其脱下一条裤腿时开枪,也是一枪不中还能补第二枪;对挑水的敌军,要等其刚刚灌好第二桶水时开枪,这时敌人动作最慢,不易跑掉……
冷炮运动,不甘落后的炮手们
步兵狙击手们的出色表现,极大地刺激了志愿军炮兵部队。
▲入朝作战之初
志愿军装备的82毫米迫击炮和92式步兵炮
尽管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比不上美国人,同时志愿军总部为保证重大战役的炮火支援,对大口径火炮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总是看着步兵狙击手们每天“吃肉”,自己只能呆在一旁看热闹,连碗汤都喝不上,炮手们也是意难平,于是纷纷请战。
步枪射程毕竟有限,杀伤力不大,对付单个人员目标效果很好,而对超出步枪射程之外的目标,尤其是大目标,如运输车辆、集群人员、坦克、火炮等等,就无能为力了,只能靠炮手去收拾。
只有冷枪与冷炮相结合,方能使志愿军的狙击作战真正覆盖敌军阵地的前沿与纵深,彻底打痛、打怕敌人。
▲志愿军将山炮拆开,以手提肩扛的方式将部件扛到山顶阵地上去。
实际上,早在冷枪冷炮起步阶段,志愿军团以下部队随伴火炮已经进行了许多游动炮作战,并取得了众多战果,只不过与冷枪运动相比规模不大,气势不盛。到了1952年8月,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志愿军总部在充分肯定冷枪运动的同时,要求炮兵部队也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开展冷炮运动。
像步枪狙击手一样,冷炮作战采取的也是游动炮群作战,并且要求各种火炮门类齐全,曲射炮与平射火炮、大口径与小口径火炮都有,做到远战、近战相结合。
▲志愿军炮手
一般讲,每个军支援炮兵在每千米的正面上设置约2门火炮,每门炮的搜索地段(即射击正面)300~500米,以确保没有火力空隙。不同炮种具体任务也不同:榴弹炮和大口径迫击炮因炮弹威力大,专打敌坦克;野炮因炮弹速度快,专打敌运输汽车;迫击炮和山炮因为射击距离近,便于观测和修正射弹,专打敌班以下建制步兵群。
由于火炮目标大,转移慢,比步兵更易遭到火力报复。因此,游动炮的阵地一般选择在炮兵主阵地的侧方或前方300米以外,以野战工事为主。每门炮要有两个以上阵地,呈前后配置。炮阵地伪装每日更新。在一个阵地最多作战7天后,一定要转移阵地,以免被敌飞机发现。
冷枪与冷炮的配合,使志愿军的狙击作战威力越来越大。各种兵器依据兵器性能、目标特点,有着明确的任务区分和射击区域分工。一般讲500米以内的人员目标,由步枪狙击手负责打;500米至1000米内的单个或小群人员目标,主要是轻重机枪打,步枪配合;500米至1000米以上的车辆、工事或人员集群目标,由无坐力炮负责;1000米以上的目标,由小口径迫击炮负责,1000-1500米内的目标,由81毫米迫击炮负责;1500米-2000米之外,3000-5000米距离内的目标,由122毫米榴弹炮负责。
▲使用苏制M-1938型122毫米榴弹炮进行炮击的志愿军炮兵
各种兵器既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在敌人的阵地罩上了一张死亡之网。
冷炮运动的代表人物,非第15军第133团无后坐力炮排排长高奎和第15军第135团迫击炮连战士唐章洪莫属。
高奎非常善于操作美制M-18型57毫米和M-20型75毫米无后坐力炮,曾经用40发炮弹打掉敌军8个地堡,击毙13名敌人,成为第15军闻名的神炮手。
▲志愿军在使用缴获的M-20型75毫米无后坐力炮。
后来,由于美军纷纷龟缩进地堡和坑道不出来,于是志愿军狙击手们们来找高奎帮忙,让他想办法用炮把敌人从地堡里轰出来,好让狙击手们开开荤。
高奎开心地答应,立即跑到阵地上测算炮击位置和距离,最后在1100米的距离上,仅用M-20无后坐力炮的两发炮弹就把敌地堡炸出了一个大洞,地堡中的敌人惊慌逃出,被等候多时的狙击手们围猎,全部被消灭殆尽。
而唐章洪的故事则更为热血。作为82毫米迫击炮炮手,他在阵地上采取单炮游动作战方式,在65天时间里,仅用79发炮弹就消灭了101个敌人,很快成为全军的传奇炮手。
▲将射击诸元标记在阵地上的唐章洪
在他歼敌超过100人的那天,是1952年8月初的一个黎明,太阳刚刚升起。当时,敌人想赶在天亮前抢运物资,谁知这一切都被唐章洪用望远镜借着晨光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刻将情况报告给了排长李文堂,排长瞬间便来了精神,一把抢过望远镜亲自充当观察哨。
唐章洪则迅速跑回炮位,“嘭!嘭!”果断打了两炮。正当唐章洪因看不着弹着点心中没数时,排长李文堂一边挥舞望远镜一边大喊:“唐章洪,唐章洪,打得太棒了!至少打掉了三个敌人!”
冷枪冷炮运动中,在“三八线”200多公里长的阵地上,活跃着成百上千个志愿军狙击小组,打出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狙击作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志愿军冷枪冷炮运动共毙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5.2万余人,有效争取主动,巩固了我前沿阵地。
这一辉煌的战绩足以使志愿军的狙击手们载入世界战争的史册。
冷枪冷炮运动正是这种战争理论的完美体现。凭着中国人的智慧,志愿军用着各种已落伍的兵器,用着最聪明、最有效的战术,演出了一幕世界战争史上最匪夷所思的狙击作战。它无法决定战争的进程,但却为志愿军夺取战场主动权,进而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看过《兵临城下》《美国狙击手》等讲述苏联、美国狙击手事迹的电影。现在,我们也即将迎来讲述自己狙击手事迹的电影,幸甚至哉。而冷枪冷炮运动中涌现出的无数可爱的人和事,肯定会成为影视创作者们不竭的灵感源泉。
期待他们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铭记历史,反思战争,珍爱和平为主题的影视作品。